任光禄竹溪记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是将不胜笑也。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经游观过京城世宦富贵人家的亭园,见那里收藏的东西,从极远的边地到海外,奇异的花卉石子没有不能罗致的,所不能罗致的只有竹子。我们江南人砍伐竹子当柴烧,筑园建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奇花异石,有的用千钱买一石,有的用百钱买一花,并不吝惜。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当中,有时就将它砍去,说:“不要让它占了我种花置石的地方”。但京城人如果能觅到可心的竹子,常常不惜花费数千钱来购买;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干枯而死。正因为它的难以寻觅而且又多枯死,人们因此就更加珍爱它。而江南人中有人讥笑他们说:“京城人竞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视为珍宝。”呜呼!奇花异石诚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然而追溯它们的产地,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与竹子在江南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边地海外,或许是从不出产竹子的地方,假如让那里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爱和看重它。这种情况恐个白是笑不完的了。俗语说: “人离乡则愈贱,物离乡则愈贵。”如此说来,世上的美丑好恶,又有什么不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任光禄君在荆溪的边上构筑了一个亭园,到处种竹,不种其他的花木。竹林间造了一座小楼,有空就与客人在那里吟诗啸歌。他偶然对我说:“我不能与有势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盛况,单独在这里取山地本来所有的东西,可以不花费劳力而使满园苍翠葱茏,也足以自适。因此自称是竹溪主人。请外甥为我记述一下吧。”我认为任君哪里是真的不能与有势力者攀比,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而不愿意把它告诉别人呢?过去有人谈论竹子,以为它绝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所以它奇巧怪异不如石,妖艳柔美不如花,孑孑然有如高傲独立的士人,不能与尘俗混同合一。因此自古以来,知道珍爱竹子的人极少。那么京城人难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爱的吗?他们不过是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如同用奇花异石向人炫耀一样。所以京城人的珍爱竹子,与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们都算不上懂得竹子。
任君在繁华闹市中生长,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饰、车马、僮仆、歌舞,凡是富贵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摒弃而去。尤其是方正刚直不随意与人交往,凛然有高洁独立之气,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那么虽然假使竹子不是这里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将竭尽其力予以收集,然后心里才高兴。任君的财力虽然使他能尽量寻觅奇花异石,然而他的爱好本不在此啊。可叹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为人贵重,对此我更加有感受了。
注释
任光禄:任氏,名卿,字世臣,号竹溪,宜兴人,生于明宏治戊午五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甲寅八月初十日。曾历任光禄寺署丞、湖广都御史等职。所居皆艺竹,故号竹溪。
光禄:官名,光禄寺卿或少卿。
绝徼(jiào):极远的边地。
徼:边界。
芟(shān):锄除。
去:去除。
是:这。
穷其所生之地:探求它的原产地。穷:追溯。
去乡:离开本土。
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世人对于美丑的看法,是不固定的。
荆溪:水名,在江苏南部,经溧阳、宜兴,注入太湖。
间:间隙,这里指偶然。
土:这里指本土,本地。
蓊(wěng)然:丛密的样子。
臭(xiù)味:气味。
绰约:柔美的样子。
孑(jié)孑然:形容孤高的样子。
偃蹇(jiǎn):高傲的样子。
谐:协调。
一:一样的。
纷华:指富贵繁华的生活。
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间:间隔,阻止。
然则:既然这样……那么。
重:甚。
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参考资料:
赏析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参考资料:
唐顺之(公元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抗倭英雄。 正德二年十月初五出生在常州(武进)城内青果巷易书堂官宦之家。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1560年四月丙申(初一)日(4月25日)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荆川先生"。
鳞介无小大,遂性各沉浮。
突兀海底鳌,首冠三神丘。
钩网不能制,其来非一秋。
或者不量力,谓兹鳌可求。
屃赑牵不动,纶绝沉其钩。
一鳌既顿颔,诸鳌齐掉头。
白涛与黑浪,呼吸绕咽喉。
喷风激飞廉,鼓波怒阳侯。
鲸鲵得其便,张口欲吞舟。
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
遂使江汉水,朝宗意亦休。
苍然屏风上,此画良有由。
潦倒宦情尽,萧条芳岁阑。欲辞南国去,重上北城看。
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
插雾峰头没,穿霞日脚残。水光红漾漾,树色绿漫漫。
约略留遗爱,殷勤念旧欢。病抛官职易,老别友朋难。
九月全无热,西风亦未寒。齐云楼北面,半日凭栏干。
第一折
(冲末扮殿头官领张千上,云)淡淡濛濛映晓星,海潮捧现日东升。九重阊阖开宫殿,文武班齐贺圣明。小官殿头官是也。方今大汉,圣人在位,节俭宽洪,施恩布德,过尧舜之治化,迈汤武之宽仁。礼乐修明,彝伦叙正,感应的天下咸宁,八方肃靖。东夷西戎仰化,南蛮北狄归降。贡麟凤献瑞呈样,产禾苗丰年稔岁。自大汉以来,立社稷之坚固,保家邦之永昌。俺汉国乃建都之地,锦绣山河。到春来赏韶华霁景,步绿野红尘,往来车马争驰,赏不尽花光柳色。到夏来玩江山明媚,宴水阁凤亭,荷莲香满池塘,处处竹林松径。到秋来凉生暑退,登云岭层楼,赏黄花四野铺金,真乃是山明水秀。到冬来木凋松秀,赏雪寻梅,涤场圃讲武操兵,享富贵红炉暖阁。端的是四时花烂漫,八节景稀奇。乃鱼龙变化之乡,锦绣繁华之地。文臣善治安民,武将施谋定乱。方今圣人任贤使能,崇儒重道,好礼尚文,乃仁德之君也。小官忝掌朝纲之事,乃职所当为。今日早朝,奉圣人的命,为因朝中缺少文武英才,着小官访能干官员,去天下府州县驿,山间林下,但有文高武胜之人,荐举于朝,必当擢用。小官领了圣命,今差使臣天下采访去了。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圣人的话,走一遭也。圣人宽洪治万邦,纷纷四海隐贤良。怀才抱德须当用,保举于朝作栋梁。(下)(外扮蔡员外同卜儿领家童上)(蔡员外云)富贵荣华祖辈传,常行方便自然安。家生一子行忠孝,宝鼎香焚答谢天。老夫姓蔡,名宁,字以静,本贯汝南人也。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婆婆延氏,所生一子,乃是蔡顺,年二十岁也。孩儿幼习儒业,涉猎经史,讲明圣人经书,饱谙古今事理,学成满腹大才。为因父母在堂,未肯求进。媳妇儿李氏润莲,他乃宦门之女。这孩儿三从四德为先,贞烈贤达第一。针指女工,无不通晓。蔡顺与润莲十分孝道,昏定晨省,问安视寝,侍奉亲闱,无些须敢慢。老夫积祖以来,家中颇有赀财。老夫平素之间,多行善事,广积阴功。发慈悯布德施恩,行仁义宽洪海量。爱交善友良朋,并无邪僻之事,人皆员外呼之。时遇盛冬天气,朔风大凛,密布彤云,纷纷扬扬,下着这国家祥瑞。老夫今日在映雪堂上,安排酒筵,请几个年高长者,赏雪饮酒,取一时之乐。婆婆,酒肴之类,安排的停当了不曾?(卜儿云)老员外,我早间分付下兴儿,着他买些新鲜的按酒稀奇果品,不知停当了不曾?下次小的每,与我唤的兴儿来者。(家童云)理会的。(净扮兴儿上,云)自幼乖觉伶俐,不与儿童作戏。专以志诚为本,所事合着人意。醉了时丢砖掠瓦,到晚来飞檐走壁。常着人摔翻踢打,
酒醒时后悔不及。气的我满腹疼痛,嗤嗤的则放大屁。猛可里一声响亮恰似我员外出气。(外呈答云)得也么?看这厮。(兴儿云)小人是蔡员外家中兴儿便是。时遇暮冬天气,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老员外不惜资财,在映雪堂上安排酒肴,请他那一般富豪长者,赏雪饮酒,施展他那富贵奢华。早间夫人分付,着我买些新鲜的按酒,与了俺十两银子,着我买办,我倒落下他七两九钱八分半。酒肴都预备停当了,员外在映雪堂上呼唤,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做见科,云)老员外唤兴儿怎么?(员外云)兴儿,我今日要赏雪饮酒,果卓都安排下了么?(兴儿云)员外,今日早间,奶奶分付了我一声,我打了个料帐,去那街市上,不一时把那应用的按酒果品,都买将来,安排的水陆俱备。别的不打紧,我七钱银子买了一只肥鹅,您孩儿是孝顺的心肠,着我自家宰了,退的干干净净的,煮在锅里,煮了两三个时辰。不想家里跟马的小褚儿走将来,把那锅盖一揭揭开,那鹅忒楞楞就飞的去了。(外呈答云)诌弟子孩儿。(兴儿云)我不敢说慌。我要说慌,就是老鼠养的。(外呈答云)得也么,泼说。(蔡员外云)这厮胡说。一壁厢预备果卓,家童门首觑者,若众长者来时,报复我知道。(家童云)理会的。(刘普能同周景和上)(刘普能云)瑞雪飞扬满太空,黎民深喜庆年丰。收成米麦盈仓廪,弦管笙歌乐盛冬。老夫姓刘,双名普能。这一位长者,是周景和。老夫幼习儒业,颇看诗书。田园数处,家道丰盈。牛羊孳畜成群,地方广阔千顷。非干老夫之能,托赖祖宗之阴也。时遇扬风搅雪,下着国家祥瑞。本处蔡员外,安排酒肴,请众位长者,在映雪堂上,赏雪饮酒。周景和,俺须索走一遭去。(周景和云)长者,时值严凝天气,朔风凛冽,瑞雪纷纷。这雪似梨花乱落长空,如柳絮飘扬霄汉。长者乃豪富之家,正好赏雪饮酒,同席欢会,俺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家童报复去,道有刘普能、周景和来了也。(家童云)理会的。(报科,云)报得员外得知,有刘普能、周景和来了也。(蔡员外云)道有请。(家童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刘普能云)呀、呀、呀,老员外,量俺二人有何德能,着员外置酒张筵。俺难以克当也。(蔡员外云)不敢,不敢。二位长者,少待片时,等众位长者来全了时饮酒。这早晚敢待来也。(夏德闰、仇彦达上)(夏德闰云)盛世丰年宇宙清,万民安乐尽康宁。天公幸际垂祥瑞,酒泛羊羔享太平。老夫姓夏,双名德闰。这一位长者,是仇彦达。老夫幼习经典,勤于学问。祖代留传,家私广盛。一年收十载余粮,一倍增万倍之利。方今圣人在位,
治平天下,肃靖边庭。感应的风调雨顺,大收禾稼。此时岁稔年丰,老夫当享太平之世。时遇冬暮天道,纷纷扬扬,下着如此般大雪。有本处蔡员外,是吾故友,在映雪堂上,请众位长者,赏雪饮酒。仇彦达,俺须索走一遭去。(仇彦达云)长者,这般大雪非常,方今太平盛世,此雪是国家之吉兆,单应来春天下青苗皆发,必然大收也。(夏德闰云)言者当也,俺一同赏去来。可早来到也。家童报复去,道有夏德闰、仇彦达来了也。(家童云)理会的。(报科,云)报的员外得知,有夏德闰、仇彦达来了也。(蔡员外云)道有请。(家童云)理会的。有请。(见科)(夏德闰云)有劳长者设此华筵,俺二人不胜感戴也。(蔡员外云)不敢,不敢。您二位长者,且待片时,等众员外来全了时饮酒。这早晚敢待来也。(二净扮王伴哥、白厮赖上)(王伴哥云)小子一生不受苦,外貌端庄内有福。我吹的龙笛品的箫,打的筋斗擂的鼓。我两个一生皮脸无羞耻,油嘴之中俺为祖。人家摆酒未邀宾,我仗着村浊性儿鲁。走到人家则管口赛,酒肉装满咱肚腹。我这个兄弟,他把骆驼一口咬断了筋,我在下把那癞象一口咽见了骨。这个兄弟嘴馋起来似饿狼,我在下嘴馋起来如病虎。我绕门踅户二十年,俺两个吃倒泰山不谢土。(外呈答云)馋弟子孩儿,得也么?(王伴哥云)自家姓王,双名是伴哥。这个兄弟姓白,双名是厮赖,又唤着白吃白嚼白口赛。(外呈答云)得也么?(王伴哥云)他新取了个媳妇,就唤做白萝卜儿。(外呈答云)得也么?(王伴哥云)俺两个是至交的好弟兄,绝伦的光棍。平日之间,别无什么买卖,全凭着舌剑唇枪,说嘴儿哄人的钱使。我这两兄弟,又比我能言快语。(白厮赖云)我说哥你少嘴舌罢。量你兄弟,不是贤兄挂齿,哥的那喉舌,何人敢及?古者有随何、蒯通、苏秦,虽为舌辩之士,若是见了哥,也拱手回容,他岂敢开口?量您兄弟拙口钝腮,真乃蛆皮而已。我若虚言,哥就是我的孙子。(外呈答云)这厮要便宜。得也么?(王伴哥云)兄弟,闲话休题。今日下着这般大雪,俺身上都单寒,肚里骨碌碌的响绕动了。我心上要吃些茶饭,手里又无钱,可怎么好?(白厮赖云)哥,有了主儿了,我着你饱吃一顿。(王伴哥云)兄弟,你敢请我?(白厮赖云)哥,你也不知道,蔡员外家安排酒席,在映雪堂上,请他一般儿富贵长者,赏雪饮酒哩。(王伴哥云)兄弟,这个是天假其便,也是俺两个甚口食分,撞席儿去。可早来到,俺自过去。(见科)(王伴哥云)众位长者支揖,恕俺两个来迟,休要见怪。若是见怪,先拿酒来,罚我几碗酒罢。(外呈答云)得也么?你看这厮。
(白厮赖云)哥,我不要罚酒,着他捣蒜蘸胖蹄,我们先吃一顿。(蔡员外云)你两个休要搅扰。家童抬过果卓来者。(家童云)理会的。(抬果卓科)(蔡员外云)将酒来。(家童云)理会的。(蔡员外递酒科,云)众位长者,想圣人治世,普施洪恩,大行王道。见如今四夷咸伏,天下平定,君圣臣贤。万民欢乐。时遇盛冬天气,下着国家祥瑞。俺遇此丰稔之时,莫负眼前光景。老夫在此草舍,聊备小酌,敬请众位长者,盘桓一会,共赏国家祯祥,方表交情。悉皆欢饮,勿劳推辞。这一杯酒,先从刘普能长者起。长者满饮一杯。(刘普能云)老长者请。(蔡员外云)长者请。(刘普能云)不敢,老夫饮。(做饮科)(蔡员外云)再将酒来。这一杯酒,周长者满饮此杯。(周景和云)不敢,老夫饮。(做饮科)(蔡员外云)再将酒来。夏长者满饮一杯。(夏德闰云)不敢,老夫饮。(做饮科)(蔡员外云)再将酒来。仇长者满饮一杯。(仇彦达云)不敢,老夫饮。(做饮科)(王伴哥云)我说老蔡,你我们两个,也看不在眼里。好酒好肉,则与别人吃,不睬我两个。你有手,我没手?你不与我递酒,我自家不会吃?(王伴哥拿酒壶科,云)众位长者请酒了。罢、罢、罢!我嘴对嘴吃罢。(外呈答云)不像样,得也么?(白厮赖云)哥吃酒,我播菜儿。(做拿下饭与王伴哥递科)(王伴哥张口科)(白厮赖自吃科,云)香喷喷的米罕。(外呈答云)两个馋弟子孩儿,得也么?(蔡员外云)酒且慢行。家童与我唤蔡顺两口儿来,与众长者行一杯酒者。(家童云)理会的。(正末扮蔡顺同旦儿上)(正末云)小生姓蔡,名顺,字君仲,本贯汝南人也。嫡亲的四口儿家属,浑家李氏,一双父母年高。小生幼习文墨,苦志于寒窗之下,学成满腹文章。为因父母在堂,未曾进取功名。小生每行孝道,侍奉双亲。想人子立身,莫大于孝。孝乃百行之源,万善之本也。时遇暮冬天气,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的祥瑞。有父亲在映雪堂上,请众长者赏雪饮酒。家童唤俺两口儿。大嫂,须索走一遭去。当今圣人在位,是好丰稔之年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见如今雨顺风调,万民安乐,年光好。圣德过尧,则他这文共武行忠孝。(旦儿云)蔡顺,是好雪也。恰便是银妆成世界,粉填满山川。这雪润陇亩,滋禾稼,天下黎民皆喜也。(正末唱)
【混江龙】上合天道,常垂甘露润田苗。这雪单注着多收五谷,广剩仓廒。乡下农民斟村洒,城中上户饮香醪。好收成端的民欢乐,托赖着一人有庆,因此上万国来朝。
(云)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我自过去。(正末同旦儿见科)(正末亏)父亲,您孩儿来了也。(蔡员外云)蔡顺,你来了?今日下着国家祥瑞,我安排酒肴,请众位长者,赏雪饮酒。你同媳妇儿,与众位长者厮见者。(正末云)您孩儿理会的。(正末同旦儿见众长者科)(正末施礼科,云)众位尊长支揖。(旦儿云)万福。(众云)不敢,不敢。(蔡员外云)众位长者在此,非我自夸。此子蔡顺,虽无大才,颇读经典。孩儿行于孝道,不出仕于朝。那堪媳妇润莲,三从四德为先,贞烈贤达第一,朝暮问安视寝,终始无移。老夫知之于心,感于肺腑,十分的见喜。因此上唤他两口儿出来,与众长者捧一杯酒,尽老夫之情也。(刘普能云)据长者仁纯德厚,仗义疏财;富不侈其心,贵不骄其志;每行善事,多积阴功;为子者尽孝,为妇者大贤,皆是老长者修积也。(正末云)众位长者在上。凡人子侍其父母,当尽其孝敬之心。夫孝者,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盖事君则忠,事亲则孝。想父母养育之恩,至重难报。今蔡顺遵先王之道,读孔圣之书,切思父母深思,重若泰山,岂敢不行孝道也?(众云)先生说的深有理。(员外云)孩儿,你与众位长者,递一杯酒者。(正末云)理会的。大嫂执着壶,我与众位长者递一杯酒。大嫂将酒来。(旦儿云)理会的。酒在此。(正末云)这杯酒,刘普能尊长,满饮一杯。(刘普能云)蔡秀才请。(正末云)不敢,老尊长请。(刘普能云)蔡秀才,是好大雪也。顷刻云迷四野,须臾雪蔽山林。这雪蜂认梨花,采之无香;鹊迷日色,飞之无影。遇此胜时,正好围炉欢饮也。(做饮科)(正末唱)
【油葫芦】你看瑞雪纷纷满目飘,将山川粉填了,恰便似蜂蝶乱嚷舞虚嚣。撏绵扯絮飞来到,恰便似杨花乱糁空中落。(刘普能云)蔡秀才,这场大雪,那田地上万种草木,到来春都皆发生也。(正末唱)这场雪润良田万物生,压瘴气滋稼苗。端的是遍街衢蔽阻长安道,恰便似风内剪鹅毛。
(云)再将酒来。这杯酒可是周员外,满饮一杯。(周景和云)好波!将来老夫饮。蔡秀才,幸际太平时世,岁稔年丰,感谢天公,降宜时瑞雪,俺正好开筵饮酒也。(正末云)老员外道的是也。(唱)
【天下乐】正值着千稔年光瑞雪飘,正好饮香也波醪。将珍羞摆列着,乐醄醄宴赏直到晓。宝鼎内香篆焚,暖炉中兽炭烧,俺可也尽开怀无处讨。(云)兴儿,将热酒来。(兴儿云)小哥,递些促掐酒儿。众位老员外,都是冻了。嘴头子热酒烫肿了,着他怎么吃下饭?(外呈答云)得也么?泼说。(正末云)这杯酒,夏员外满饮一杯。(夏德闰云)秀才请。(正末云)不敢,老员外请。(夏德闰云)秀才,这场大雪,非比寻常。恰便是空中糁玉,云外飞琼。冷飕飕行人迷径,白茫茫归鸟失巢。似这等红炉暖阁之中,理当赏雪饮酒也。(正末云)这雪越下的大了也。(唱)
【醉中天】这雪更塞拥蓝关道,尽蔽了九重霄,岭畔寒梅恰便似舒玉梢。(云)将酒来,仇员外满饮一杯。(仇彦达云)老夫饮。这雪真乃国家祥瑞也。(正末唱)这雪普四海添吉兆,仰圣德黎民安乐。满斟白醪,贺丰年万姓歌瑶。
(王伴哥云)白厮赖,恰才老蔡不与俺两个递酒。你看小蔡儿,也轻慢俺两个,也不递酒。他小觑俺两个。罢了,气杀也。(白厮赖云)哥不要上气,你若上气,显的就不是旧油嘴了。拿大碗来,倒着酒则管吃。灌的醉了,就打铺在那家里睡。哥,等他爷儿每若无礼,我把他鼻子都咬下他的来。(外呈答云)贼弟子孩儿,得也么?(蔡员外云)酒且慢行。众位长者,非老夫敢僭。则这般饮酒,也不能取其乐。列位长者,都是通文达理的人。幸遇冬寒雪降,指雪为题,每人吟一首诗。有诗者不饮酒,无诗者罚一杯。(仇彦达云)老长者,先从谁起?(蔡员外云)先从刘普能长者起。(白厮赖云)我说老蔡递酒也从他起,吟诗也从他起。他是那一个?他无故则是刘普能。他就是普贤菩萨,我也不让他。(王伴哥云)兄弟说的是。先从你起,你了是我,我了是你。两个油嘴胡说,到底吃的醉了,一齐调鬼。(外呈答云)泼说。(刘普能云)今蒙长者大设华筵,重意相待。老长者单指雪为题,要俺俱各吟诗一首,无诗者罚酒一杯。众位长者恕罪,老夫不才,强搜枯肠,作诗一首,众位长者污目者。(众云)不敢,不敢。洗耳愿闻。(刘普能吟诗,云)碎剪琼花满太空,彤云万里布寒风,拥炉画屋如春暖,诗酒高谈乐盛冬。(众云)高才,高才!(王伴哥云)他便高才,吃了酒了,可不高才。(外呈答云)不高才吃打。得也么?(周景和云)该老夫吟诗也。我诗就了,众位长者恕罪。(众云)不敢,不敢。洗耳愿闻。(周景和吟诗,云)蝶翅飞扬落地轻,风翻柳絮舞零零。滋禾润稼呈祥瑞,万姓讴歌乐太平。(众云)高才,高才!(白厮赖云)高裁做的好衣服。(外呈答云)怎的?(白厮赖云)我说是高裁。(外呈答云)那个高才,得也么?(夏德闰云)该老夫吟诗。我诗就了也,众长者恕罪。(众云)不敢,不敢。(夏德闰吟诗,云)扑面穿帘拂粉墙,飞琼糁玉六花扬。高堂映雪宜欢饮,烂醉笙歌锦瑟傍。(众云)高才,高才!(王伴哥云)我可是他能饮的伯伯。(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仇彦达云)该老夫吟诗。我诗就了也,众位长者恕罪。(众云)不敢,不敢。(仇彦达吟诗科,云)一色楼台尽粉妆,随风逐物弄轻狂。低垂帘幕陈佳宴,笑饮忘怀入醉乡。(众云)高才,高才!(白厮赖云)我可其实的快口赛。(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蔡员外云)众位长者,高才大德,博学广文,真乃古君子也。老夫疏于学问,草腹莱肠,对着众位长者,也吟诗一首,万望勿哂者。(众云)不敢,不敢。愿闻。(蔡员外云)老夫吟诗也。(做吟诗科,云)密布彤云遍九霄,飞空四野剪鹅毛。羊羔酒泛歌金缕,共享丰年乐事饶。
(众云)高才,高才!(正末云)众位老尊长在上,小生无才,也吟诗一首,以尽人之欢也。诗中之意,倘有不周,望众位长者教训者。(众云)不敢,不敢。愿闻。(正末云)小生吟诗也。(做吟诗科,云)凛凛寒风透满怀,遥空顷刻冻云埋。纷纷祥瑞天街落,四海消除黎庶灾。(众云)高才,高才!(王伴哥云)他甚么高才?老蔡,我把你个老猢狲。我两个是客人,倒不让俺吟诗。你爷儿两个是东主,你倒先吟了诗。你意思道他两个是愚鲁之人,不知文义,小量俺两个。不是俺骗你那驴嘴,我把那五言诗八韵赋,长篇短文,我作了勿知其数。量这首雪诗,有何罕哉?拿酒来,我吃一碗,然后吟诗。若吟的不是,每人再罚我一碗。(外呈答云)得也么?倒好了你也。(王伴哥云)我吟诗也,众位长者勿罪。(做吟诗科,云)纷纷瑞雪满阶基,有似杨花上下飞。一轮红日当天照,管情化做一街泥。(外呈答云)可知是一街泥,得也么?(白厮赖云)好,哥也不枉了吟的好诗。真乃是文章的魁首,油嘴的班头。(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白厮赖云)古人说:凡会酒席吟诗,不可太多。我学生不吟诗,我如今指雪为题唱个小小的曲儿,曲子名是〔清江引〕,众位长者污耳者。(众云)你唱,你唱。(白厮赖云)曲儿不打紧,听我的歌声宛转。上古秦青善能歌唱,他若听见我唱,他也拱手而伏。众位长者,听我唱赏雪的曲儿。(唱)
【清江引】这雪白来白似白厮赖,(云)这雪若还下在席子上,(唱)恰便似一床白绫被。铺在热炕上,盖着和衣儿睡,醒来时化了一身水。
(外呈答云)诌弟子孩儿,不甚好。得也么?(夏德闰云)众长者,似这等寒冬雪降,那富豪之家,暖阁内簌毡帘,围炉中烧兽炭,银瓶内斟美酒,轻裘暖帽,骏马雕鞍,富贵任其所愿。有那等贫寒之家,身无遮体之衣,口无应饥之食,战战兢兢,无颜落色,冻剥剥的袖手低头。蔡秀才,你是读书的人,想人生于世,有钱的可是怎生?无钱的可是何如?你试说。我试听者。(正末唱)
【那吒令】有钱人最好,锦貂裘暖帽;无钱人困遭,穿补衣衲袄;绕人家乞讨,忍饥寒冻倒。数九天怎过遣?大街上高声叫,战兢兢性命难逃。(夏德闰云)人生在天地之间,贫富分其两等,乃自然之理也。(正末唱)
【鹊踏枝】富家郎逞英豪,显奢骄,他每便语话言谈,气势偏高。腆着脯向人前气傲,他把这贫民每当作儿曹。
(仇彦达云)秀才言者当也。便好道:衣是人之威,钱是人之胆。今时人,享荣华,受富贵,穿锦绣,住兰堂,乃前生分定也。(正末云)这贫寒富贵,非同小可。(唱)
【寄生草】有钱的高堂上常奢侈,无钱的遭贫寒居瓦窑。有钱的列金钗弦管可便心欢乐,无钱的受忄西惶寂寞伤怀抱。有钱的逞轩昂马践红尘道,无钱的向人前缩手口难开,则他这贫穷富贵是天道。(蔡员外云)众位长者,慢慢的饮酒。看有甚么人来?(解子押延岑上)(延岑云)猛烈刚强自古无,平生慷慨不尘俗。见义当为真男子,则是我正直无私大丈夫。某姓延,名岑,字均义。我早生好汉,刚强性鲁,膂力过人。我在那长街市上闲行,因见个年少的后生,赶着个年老的打。我路见不平,将那年少拉将过来,三拳两脚,过打死了。我出首到官,饶我死罪,脊杖了六十,罚我去郑州迭配牢城。时遇冬暮天气,纷纷扬扬的下着这般大雪,身上单寒,肚里无食。解子哥哥,你看这家儿人家,高房子,大门楼,门前马车嚷闹,必是个豪富之家。俺去讨些茶饭食用。(解子云)延岑,你可休走了。(延岑云)哥哥,小人身做身当,岂敢带累你也?(解子云)你若这般,便好。(延岑云)来到门首也。我试叫一声。大主人家,有那怜悯之心,用不了的茶饭,乞讨些食用。(正末云)甚么人在门首,大惊小怪的?我试看去者。(蔡员外云)孩儿也,你试看去。(正末出门见科,云)一条好汉也。兀那壮士,你因何带锁披枷来?(延岑云)哥哥不知。小人平昔之间,刚强怀勇,膂力过人。一日街上闲行,见一个年少后生,赶着个年老的打。我路见不平,把那年少的拉将过来,三拳两脚打死了。我出首到官,免我死罪,脊杖了六十,罚去郑州迭配牢城。身上单寒,肚中饥馁。路打门首过,见车马盈门,小人来乞讨些茶饭食用。(正末云)壮士,你少待片时。(正末进门科,云)俺这家私里外,无人照管。若得这个壮士,与我做护臂,可也好也。我对父亲母亲说去。(正末见蔡员外科)(蔡员外云)孩儿也,甚么人吵闹?(正末云)父亲,门首有小壮士,迭配郑州牢城去。身上单寒,肚中饥馁,来乞讨些茶饭食用。父亲,俺家私卫外,无人照觑。若得这个壮士,与我做了护臂,可也好也。(蔡员外云)孩儿也,与我唤过那壮士来。(正末云)理会的。(正末见延岑云)兀那壮士,俺父亲唤你哩。(延岑云)理会的。(见众长者科,云)众位老长者,小人施礼哩。(蔡员外云)兀那壮士,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甚带锁披枷?你说一遍者。(延岑云)小人姓延,名岑,字均义,乃济州历阳人也。我平日之间,刚直性勇,膂力过人。忽朝一日街上闲行,见一个年少的后生,赶着年老的打。我路见不平,将那年少的,三拳两脚打死了。小人出首到官,免我死罪,脊杖了六十,罚去郑州迭配牢城。下着如此
般大雪,身上无衣,肚里无食。路打长者门首过,见车马盈门,特来乞讨些茶饭食用。(蔡员外云)哦!原来是这般。兴儿将热酒来,着壮士饮几杯。(兴儿云)烫口的热酒。(蔡员外云)来、来、来,壮士,你满饮一杯。(延岑云)老长者,量小人有何德能,着长者这等错爱?(蔡员外云)壮士,你在患难之中,不必多念。兴儿,将些茶饭来,着壮士食用。(兴儿云)老的也,留着好酒肉待客人,与他吃怎么?看他两个眼,剔留秃鲁的,他是个真贼。(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兴儿拿茶饭科,云)来、未、来,一盘卷子,一盘羊肉,你吃、你吃。(延岑云)解子哥哥,你吃一杯酒,吃些茶饭波。(解子云)我饿过了,吃不下也。(卜儿见蔡员外,云)老的,我有句话,可敢说么?(蔡员外云)婆婆有甚么话说?(卜儿云)老身姓延,这个壮士也姓延。我想来一般树上,那得两般花,俺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有心认义他做个侄儿,未知老的意下如何?(蔡员外云)婆婆,你心与我皆同,不知这壮士心下如何?你试问他者。(卜儿云)兀那壮士,老身姓延,你也姓延。俺老两口儿,止生了这个孩儿是蔡顺。我想来,一般树上,那得两般花,俺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有心认义你做个侄儿,你意下如伺?(延岑云)奶奶,你休逗小人耍。(卜儿云)我见你英雄,并无假意。(延岑云)是真个?多谢了父亲母亲也。(卜儿云)蔡顺,您两个拜你哥哥者。(正末云)哥哥受俺两口儿一拜。(延岑云)兄弟,多谢父亲母亲,一见如故。此恩重如泰山,异日峥嵘.此恩必当重报也。(正末唱)
【金盏儿】哥哥你是英豪,逞雄骁。(延岑云)兄弟,我路见不平,把那年少的三拳两脚,就打死了也。(正末唱)致伤人命官司行告,郑州迭配见些功劳。有一日身荣为官爵。青史把名标。博一个马靴白象简,金带紫罗袍。
(解子云)这早晚雪下的大了。延岑,俺还要赶程途哩。辞了长者,俺去来。(蔡员外云)家重将来。(家童拿砌末科,云)理会的。(蔡员外云)延岑,与你这一套暖衣,十两银子,做盘费。解子哥哥,与你这五两银子,路上看觑他者。(解子云)谢了长者,小人知道。(延岑拜科,云)谢了父母。(卜儿云)延岑,你路上小心在意者。(延岑云)父亲母亲,您孩儿只今便索长行。久以后不得峥嵘发达便罢,但得一身显耀,您孩儿口中衔铁,背上搭鞍,报今日父母之恩。哥哥、嫂嫂,善侍父母。众位长者恕罪。我出的这门来。解子哥哥,我想来,谁想今日,遇着这一家人家,将我认义做亲,与我衣服钱钞。此恩异日必当重报也。只因刚强性不容,致伤人命入牢城。异日风光身显耀,必报今朝济惠恩。(同下)(刘普能云)蔡长者,量俺有何德能,着长者重意相待。俺酒够了也,长者夫人告辞。(蔡员外云)普能再饮一杯。(刘普能云)不必了,长者恕罪,我出的这门来。周景和,天色晚了也,俺一同回去来。瑞雪纷纷四野垂,围炉开宴捧金杯。知心故友同酬兴,满头风雪醉扶归。(同下)(夏德闰云)刘普能、周景和他二人去了,仇彦达,俺也回去来。长者恕罪。出的这门来,天色晚了也。深蒙良友大张筵,美酒盈樽喜笑喧。忘杯横饮无拘系,不负三冬瑞雪天。(同下)(王伴哥云)白厮赖,他四位长者,都回去了。俺两个每人再吃两碗回去罢。(白厮赖云)哥也,俺打刺孙多了,您兄弟莎搭八了,俺牙不约儿赤罢。(外呈答云)且打番语,得也么?(王伴哥云)依着兄弟回去来。今日个俺来油嘴,吃东西恰是饿鬼。我如今跑到家里,再吃上五碗雪三盆凉水。(二净下)(蔡员外云)众位员外都回去了也。夫人媳妇儿,无甚事,俺回后堂中去来。(正末云)父亲?俺回后堂中去来。(唱)
【尾声】俺可便离了画阁兰堂,举步登途道,赏瑞雪排筵罢却。(蔡员外云)孩儿也,为人在世,得欢当作乐,莫负眼前光景也。(正末唱)咱人便休把时光虚度了,(蔡员外云)今日赏雪饮酒,都皆沉醉也。(正末唱)尽今生乐酶酶,饮香醪,满捧羊羔。宝鼎龙涎香未消,则他这银台上蜡烧。他每都觥筹欢笑,(旦儿云)蔡顺,今日父母十分欢喜也。(正末云)俺为子者,要孝当竭力也。(唱)则愿的一双父母寿年高。(同下)
第二折
(卜儿抱病同蔡员外领净兴儿、旦儿上)(卜儿云)四肢老弱身无力,呵吁,两鬓斑皤病已深。老身延氏,为因上庙烧香去,我赶头香,起的早了些儿,感了些寒气,一卧儿不起,饮食少进,睡卧不宁。争奈老身年纪高大,肌体尫羸,我那里耽的这般病证?这两日身心恍惚。老的也,我的病越沉重了也。(蔡员外云)婆婆,便好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这病是轻灾浮难,不必忧心。婆婆,将息病体,省可里烦恼也。(卜儿云)媳妇儿,蔡顺孩儿那里去了也?(旦儿云)蔡顺去街市上,与婆婆请医士去了也。(蔡员外云)婆婆,想人皆养子,无过蔡顺孝。俺幸遇此子,立身壮志.正好同堂欢乐。婆婆,你耐心守病也。(卜儿云)老的也,我这病有添无那减了也。媳妇儿,等孩儿来时,报复我知道。(旦儿云)理会的,我在门首望者,蔡顺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上云)小生蔡顺是也。为因老母,庙上烧香,感了些风寒,见今病枕着床。嗟乎!年纪高大,肌体尫羸,值此病证。俺为子者何忍乎?小生对天祷告:愿将己身之寿,减一半与母亲。愿母亲寿活百岁有余,方表人子之孝也。小生为母不安,这些时衣不解带,废寝忘餐,忧凄不止。似此可怎了?小生恰才去那周桥左侧,请下个医士,调治母亲的病证,太医随后便来也。小生见母亲,走一遭去。蔡顺也,切思老母养育之恩,何以报答也?(唱)
【商调】【集贤宾】则俺那老萱亲在堂年迈高,小生我想恩养育痛悲号。俺母亲偎于湿三年乳哺,更怀耽十月劬劳。我母亲抬举的立志成名,生长的貌类清标。方信养生送死防备老,忆深恩我未报分毫。谁承望尊堂病已深,则俺这幼子泪如浇。
(兴儿云)小哥少烦恼,奶奶年纪高大了也。奶奶睡倒身疲倦,起来不思馔。心恍神不宁,头晕眼睛转。脸上皱纹多,手上青筋乱。你若到家中,奶奶不死也气断。有的性命活,也是棺材楦。(外呈答云)贼弟子孩儿,得也么?(正末云)阿!好是烦恼人也呵。(唱)
【逍遥乐】俺母亲骨岩岩身躯老耄,(带云)叹母亲这病,(唱)恰便似风里杨花,水亡幻泡。(兴儿云)小哥不要心焦,到家里把奶奶的病,我替他害了罢。(正末唱)好教我便展转的添焦,俺母亲眼睁睁病枕难熬。我可便心似油煎身如火燎,仰穹苍痛哭嚎啕。(带云)蔡顺一片孝心,惟天可表也。(唱)则愿的母病安妥,父命延长,子寿愿夭。
(云)来到门首也。(见旦儿科,云)大嫂,你在这里做甚么?(旦儿云)蔡顺,母亲这一会儿,觉沉重了也。恰才唤你来,我说你请太医去了。你过去见母亲去。(正末云)似此可怎了也?我去见母亲去。(做见卜儿科,云)母亲,您孩儿恰才周桥左侧,请下个高手的医者,便来调理母亲的病证。母亲,今日病体如何?(卜儿云)孩儿,我这一会儿不见你,不由我心中思想。我这病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蔡员外云)孩儿也,你母亲寿年高大,值此风雪之寒,寝馔俱废,朝暮不能动履,命在顷刻之间,岂能相保?孩儿,如此如之奈何?(正末云)父亲,岂不闻圣人云:父母有疾,人子忧心,无所不用其情。怎敢时刻懈怠也?想母亲止生您孩儿一个,今立身成名,岂不知父母鞠养之恩?您孩儿为母不安,这些时衣不解带,寝食俱废,忧凄不止,行坐之间,犹如失魂丧魄。您孩儿对天祷告:愿将己身之寿,减一半与母亲,愿母亲寿享百岁有余,方称您孩儿之愿也。(卜儿云)孩儿也,想人子之心,奉母莫大于孝。你的孝情,我尽知也。今老身命已将危,乃人之大限,你父子免劳忧虑。儿也,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旦儿云)蔡顺,你请的太医,这早晚不见来?(正末云)大嫂,预备下茶汤,太医这早晚敢待来也。(正净扮太医上,云)我做太医最胎孩,深知方脉广文才。人家请我去看病,着他准备棺材往外抬。自家宋太医的便是,双名是了人。若论我在下手段,比众不同。我祖是医科,曾受琢磨。我弹的琵琶,善为高歌。好饮美酒,快口赛肥鹅。那害病的人请我,我下药就着他沉疴。活的较少,死者较多。(外呈答云)名不虚传,得也么?(太医云)我这门中,有个医士,姓胡,双名是突虫,他老子就唤是胡萝卜。我和他两个的手段,也差不多,俺因此上结为兄弟。有人家来请我看病,俺两个一同都去的,少一个也不行。我看病,兄弟便下药;兄弟看病,我便下药。俺两个说下咒愿:有一个私去看病的,嘴上就生僵疙疸。今日有本处蔡秀才来请我,说他母亲害病,请我去下药,我使人约兄弟去了也。我在周桥上等着兄弟,这早晚敢待来也。(净扮糊突虫上,云)我做太医温存,医道中惟我独尊。若论煎汤下药,委的是效验如神。古者有卢医扁鹊,他则好做我重孙。害病的请我医治,一贴药着他发昏。(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糊突虫云)在下是个太医,姓胡,双名是突虫,小名儿是胡十八,祖传三辈行医。若论我学生的手段,我指上不明,医经不通。人家看病,先打三钟两碗瓶酒,五个烧饼,吃将下去,就要发风。看病不济。我吃食倒有能
。(外呈答云)两个一对儿,得也么?(糊突虫云)我这医门中有个医士,姓宋,双名是了人。俺两个的手段,都塌八四,因此上都结做弟兄。他为兄,我为弟。人家来请看病,俺两个都同去,少一个也不行。宋无胡而不走,胡无宋而不行。胡宋一齐同行,此为胡虎乎护也。(外呈答云)念等韵哩,得也么?(糊突虫云)早间宋先儿,使人来请我,说蔡秀才的母亲害病,请俺下药,有哥在周桥上等着我哩,见咱哥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做见科,云)哥也,你兄弟来迟,莫要见罪,若要见怪,哥就是虾蟆养的。(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太医云)你还说嘴哩?你平常派赖。冬寒天道,着我在这里久等,险些儿冻的我腿转筋。(糊突虫云)哥也,休怪您兄弟来迟。我有些心气疼的病,今日起的早了些儿,感了些寒气,把你兄弟争些儿不疼死了。你兄弟媳妇儿慌了,请了太医来,与了我一服药吃,我才不疼了。(外呈答云)你是太医,怎么又吃别人的药?(糊突虫云)我的药中吃,是我也吃了。(外呈答云)可怎么不中吃?(糊突虫云)我若吃了我自家的药呵,我这早晚,死了有两个时辰也。(外呈答云)你可是卢医不自医,得也么?(太医云)兄弟,自从俺打官司出来,一向无买卖。(外呈答云)为什么打官司来?(太医云)俺两个为医杀了人来。(外呈答云)两个一对儿油嘴,得也么?(太医云)兄弟,今日蔡长者家婆婆害病,请俺去下药。他是财富之家,俺到那里,他有一分病,俺说做十分病;有十分病,说做百分病。到那里胡针乱灸,与他服药吃。若是好了,俺两个多多的问他要东西钱钞。猛可里死了,背着药包,望外就跑。(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糊突虫云)哥也,言者当也。凭着俺两个一片好心,天也与半碗饭吃。(外呈答云)得也么?(太医云)兄弟俺去,可早来到也。报复去,道有两个高手的医士来了也。(家童云)您则在这里,我报复去。(做报科,云)报的长者得知:太医来了也。(蔡员外云)道有请。(家童云)理会的。有请。(糊突虫云)哥也,看仔细些,莫要掉将下来。(外呈答云)怎的?(糊突虫云)是!有请,有请。(外呈答云)慌做甚么?得也么?(太医云)俺是个官士大夫,上他门来看病,消不的他接待接待,就着俺过去?(外呈答云)你休要怪他,他家有病人。过去罢。(太医云)好儿,看着你的面上,老子过去罢。(外呈答云)这厮做大,得也么?(太医做让科,云)兄弟请了。(糊突虫云)不敢,兄长请。(太医云)贤弟请。(糊突虫云)兄长差矣。想在下虽不读孔孟之书,颇知先王之礼。岂不闻圣人云: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耕者让畔,
行者让路。长者为兄,次者为弟。兄乃我之长,我乃兄之弟。既有长幼,须分尊卑。先王之礼,亦不差矣。我若先行,我就是驴马畜生。真油嘴也。(外呈答云)什么文谈?得也么?(糊突虫云)不敢,不敢。吾兄请。(太医云)不敢。贤弟乃善良君子,我乃是愚鲁之人,区区无寸草之能。贤弟有九江之德,据贤弟医于病,神功效验;治于病,多有良方。贤弟乃大成之人,我乃蛆皮而已。我若先行,我学生就是真狗骨头之类也。(外呈答云)得也么?泼说!过去了罢。(做见卜儿科)(太医云)老母恹恹身不快,(糊突虫云)太医下药除患害。(太医做拿左手科)(糊突虫做拿右手科)(太医云)看俺双双把脉。(太医拿卜儿左手科)(唱)
【南青哥儿】入门来审了他这八脉,(糊突虫拿卜儿右手科)(唱)瘦伶仃有如麻秸。(太医唱)俺快把这药包儿忙解开。(糊突虫云)可怜也,脉息不好了。(唱)快疾忙去买,(太医唱)快疾忙占买。(正末云)太医,买甚么?(太医唱)去买一个棺材,(糊突虫唱)去买一个棺材。
(外呈答云)几时了,得也么?(太医拿药包儿打倒卜儿科)(卜儿云)打杀我也。(外呈答云)他是病人,怎么打他?(太医云)不防事,不防事。还好哩,还知疼痛哩。(外呈答云)不知疼痛,可不死哩?得也么?(太医云)胡先儿,他这个是甚么病?(糊突虫云)吾兄!不是我夸嘴。我恰才觑了他面目,审了他脉息,你摸他这半身子如火相似,他害的是热病。(太医云)你又胡说了。他这个脉息,跳的有一寸高,你怎说是热病?你看他这半边身子,如冰一般凉,他害的是冷病。(糊突虫云)吾兄也,不难把老人家鼻子为界,用一条绳拴在他鼻头上,把这绳儿扯下来,就地下钉个橛儿拴住。你医这左半边冷病,我医这右半边热病。吾兄弟意下何如?(太医云)好、好、好。俺两个说的明白。假似你一服药,着老人家吃将下去,医杀了这右半边呵呢?(糊突虫云)管不于你那左半边的冷病事。(太医云)说的有理。(糊突虫云)假若你一服药,着这老人家吃将下去,医杀了你那左半边呵呢!(太医云)管不干你那右半边的热病事。(糊突虫云)我说假似走了手,都医杀了呵呢?(太医云)管大家没事。(外呈答云)诌弟子孩儿,得也么?(蔡员外云)太医,你如今下一服甚么药?(太医云)我如今下一服是夺命丹,第二服促死丸。(蔡员外云)你为甚么与他两样药吃?(太医云)你不知道,我有主意。两样药吃下去,着这老人家死也死不的。活又活不的。(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糊突虫云)蔡老官儿,你要你这婆婆好么?(蔡员外云)可知要好哩。(糊突虫云)我有个海上方儿,用一庄物件,你舍的么?(蔡员外云)要我这婆婆好,不问要甚么,都舍的。(糊突虫云)把你这两只眼,拿尖刀子剜将下来,用一钟热酒吃将下去,你这婆婆就好了。(蔡员外云)他便好了,我可怎么了?(糊突虫云)你敢柱着明杖儿走。(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胡说。(蔡员外云)住、住、住,你两个休要胡厮嚷。你二位端的那一位高强?让一个医了罢。(二净拿着药包,一递一个打着念科)(太医打糊突虫,云)我能调理四时伤寒,(糊突虫打太医,云)我善医治诸般杂证。(太医云)我厅小儿吐泻惊疳,(糊突虫云)我治妇女胎前产后。(太医云)我会医四肢八脉,(糊突虫云)我会医五劳七伤。(太医云)我会医左瘫右痪,(糊突虫云)我会医紧痨慢痨。(太医云)我会医两腿酸麻,(糊突虫云)我会医四肢沉困。(太医云)我会医口苦舌涩,(糊突虫云)我会医胸膈膨闷。(太医云)我会医瘸臁跛臂,(糊突虫云)我会医喑哑痴聋。(太医云)我会医发寒发热,(糊突虫云)我会医发傻发风。(太医云)我会医水蛊气蛊,(糊突虫云)我会医头
疼额疼。(太医云)我会医胸膛上生着孤拐,(糊突虫云)我会医肩膀上害着脚疔。(太医云)老长者着俺下药,(糊突虫云)将这个老人家丧了这残生。(太医云)用凉水满满的一碗,(糊突虫云)用巴豆足足的半升。(太医云)着这一个老人家吃将下去,(糊突虫云)叫唤起满肚里生疼。(太医云)登时间直肠直肚,(糊突虫拿药包打倒卜儿科,云)泻杀这小老妈妈,也是场干净。(外呈答云)贼弟子的孩儿,去了罢!去了罢!(打二净下)(正末云)父亲,今母亲得病,积日之久。四肢无力,身体飘然,似此如之奈何?(蔡员外云)孩儿,我试问婆婆者。婆婆,你这些时饮食不进,你心中可想甚么食用?(卜儿云)老的也,我心中想一味东西食用。奈是冬寒天气,则怕无有此物。(正末云)母亲想什么食用?对您孩儿说者。(卜儿云)孩儿也,我想那春暮天桑堪子食用。但得三两枝儿吃下去,则怕我这病减了也。(正末云)既然母亲思想桑椹子食用,您孩儿不问那里,务要寻来奉侍母亲。(卜儿云)孩儿也,我这会有些昏沉。媳妇儿,扶我去后堂中去来。我冒风寒着床垂命,为子者堂前孝敬。但得那美甘甘桑椹充饥,医可了我恹恹疾病。(同下)(蔡员外云)孩儿也,你母亲思想桑椹食用。况值盛冬时节,万木凋零,便有黄金,也无处买也。你母之命,仰望神天加护。他病痛苦淹缠,良方治不痊。我暂把愁眉放,生死任从天。(下)(正末云)母亲思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寒冬天气,可那得此物来?兴儿,与我后园中快设香案,安排祭祀礼物,我祷告神天去者。(兴儿云)小哥说的是。前堂上人杂,后园中静悄悄的。问神天求的几个桑椹子,救奶奶的命。若无桑椹子,马莲子也罢,吃下去倒消食。(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正末云)来到这后园中也。兴儿,抬过香案来者。(兴儿云)理会的。(做抬香案科,云)放下这香案,摆下三牲。小哥,都有了也。(正末云)兴儿,休要打搅。你且前后执料去者。(兴儿云)我也寒冷了。小哥,你便烧香,我灶窝里向火去也。(下)(正末烧香科,云)皇天后土,三界神祗。此一炷香不为别,有母延氏,年七十五岁。见今病枕在床,积日之久,未能得愈。切思父母之恩,未尝顷刻下怀。今母亲有疾,为子者岂可不尽其心!小生这些时衣不解带,寝食皆废,忧凄不止。今母亲沉重,投药不效,空劳无功。不期母亲思想桑椹子食用。寒冬天气,朔风遍起,万木凋零,怎生得那桑椹子来?伏望神明可怜,怎生得天上降下几个桑椹子来.救济俺母亲病体痊可。愿将蔡顺已身之寿,减一半与母亲。愿母亲寿活百岁余年,方表人子之道也。百行由来孝为先,人心尽
孝理当然。椹子若能天降下,救济慈亲病体痊。(拜科)(唱)
【梧叶儿】列香案虔诚拜,设奠祀专意祷。但能够那树上发柔条,结几个桑椹子,摘将来医济的好。我这里望青霄,哎!神也保祐的母安乐呵,惟愿的可便长生不老。
(云)小生对着神天,将头也磕破了,滴下来的泪珠儿,可都成冰了。这一会儿。觉有些昏沉。我搭伏着这香案,暂且盹睡者。(做睡科)(增福神领鬼力上,云)荡荡神威气象宽,亲传敕令下瑶天。只因人子行纯孝,吾神驾雾腾云到世间。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我身居逍遥之境,自在之乡,掌管人间贵贱寿夭增福延寿之事。行善者增添福禄,作恶者减算除年。今因下方有一人,姓蔡,名顺,字君仲,其妻乃李氏润莲。他两人每行孝道,侍奉亲闱,朝暮问安视寝,未尝有懈心。他们母亲延氏,见今染病在床上,药饵不能调治。今冬寒时月,母思桑椹子食用。此人在后花园中设其香案祭物,对天祈祷,叩头出血,滴泪成冰,又愿将己身之寿,减一半与他母亲,愿他母寿活百岁有余。此人一念诚孝,通于天地,感动神灵。吾神亲传上帝敕令,将冬天变做春天。着大众神将,今夜晚间三更时分,降甘露瑞雪,满山遍峪。但有的桑树,都生桑椹子。着蔡顺摘将去,献与他母亲食了呵,他那病体必然痊可。有此人在后园中焚罢香,搭伏着吞案,盹睡着了也。恐防蔡顺不知,吾神驾起祥云,直至此人宅上托梦,走一遭去。按落云头,可早来到他家前堂上也。鬼力与我唤将蔡氏门中家宅六神来者。(鬼力云)理会的。蔡氏门中家宅六神安在?(门神、户尉上)(门神云)积善门阑瑞霭生,手执斧钺镇宅庭。刚强正直无邪僻,以此人间为正神。小圣乃蔡氏门中门神是也,此一位乃户尉之神。今有蔡顺的母亲,病枕在床,俺家宅六神不安。因蔡顺至孝,感动神明,通于天地。有增福神降临在堂,呼唤六神,俺二神见上圣去。可早来到这前堂上也。鬼力报复去,道有门神、户尉来了也。(鬼力云)理会的。报的上圣得知,有门神、户尉来了也。(增福神云)着他过来。(鬼力云)理会的,过去。(做见科)(门神云)呀、呀、呀,早知上圣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上圣呼唤小圣有何法旨?(增福神云)门神、户尉,您且一壁有者。(外扮土地、井神同灶神、净厕神上)(土地云)吾乃土地神,秉性纯和福自臻。常居正道,永镇家庭。晨昏香火,悉把吾尊。招财进宝臻佳瑞,合家无虑保安存。(井神云)吾乃井泉神,节操坚刚民自称。将流波积聚,彻底澄清。身无点污,洁似寒冰。井中常喜祯祥现,兆应家宅百事亨。(灶神云)吾乃是灶神,一家之主我为尊。终朝火燎,每日烟熏。炭头般像貌,墨锭般法身。纵然荤素不离口,争奈终日缩灶门。(净厕神云)吾乃是厕神,我一生无始终。我坐的是净桶,玩的是粪坑。尿长溺一脸,屎长污一身。何曾得闻清香味?每日人来把屁
熏。(外呈答云)两个一对,得也么?(土地云)众神都来了也。今有蔡顺母亲,病体不安。此子至孝,通于天地,感动上界。增福神在堂呼唤,不知为何?俺见上圣去。来到这前堂上。鬼力报复去,道有土地等神来了也。(鬼力云)理会得。(报科,云)报的上圣得知,有土地等神来了也。(增福神云)着他过来。(鬼力云)理会的。过去。(做见科)(土地云)呀、呀、呀,早知上圣到来,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井神云)上圣,小圣失于迎迓,勿以见责也。(灶神云)早知来到,快跑远接。跑的紧了,一定吃跌。(外呈答云)甚么文谈?得也么?(厕神云)早知上圣来到,慌忙迎笑。若还不笑,凿个藜暴。(外呈答云)两个一对泼说,得也么?(土地云)上圣,呼唤俺家宅六神有何事也?(增福神云)您六神听者:为蔡顺母见今病枕不安,药饵不能医治。他母亲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寒冬天气,无处求取。此子至孝,通于天地,感动上帝之心。今吾神传上帝敕令,特降桑椹子,救他母亲之病。恐此人不知,吾神故来托一梦警。有蔡顺在后园中,烧罢香昏沉而睡。您六神随着我托梦去来。(众云)有劳上圣下降,俺跟上圣去来。(增福神同六神见正末科)(增福神云)来到这后园中,此人真个睡着了也。我试唤他者,蔡顺!蔡君仲!(灶神云)蔡炒肉。(厕神云)蔡里虫。(外呈答云)这厮,得也么?(正末做惊醒科)(唱)
【醋葫芦】不由我战兢兢的添怕怖,悠悠的魂魄消。我则见众神祗簇拥一周遭,莫不是身边犯下甚么罪恶?(增福神云)蔡顺休惊莫怕也。(正末唱)他可便单题着咱名号,我须索从头至尾问个根苗。(跪科,云)何方大圣?甚处灵神?通名显姓者。(厕神云)上圣,这小蔡儿最促掐。他前日望着我嘴头子上放了个屁。把我牙进掉了,我正要摆布他哩。(外呈答云)这厮且打搅。(增福神云)蔡顺,俺非外道邪魔。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这六位是您家宅六神。因你母亲病体不安,寒冬天气,想桑椹子食用。为你虔诚恳祷,祈求此物,叩头出血,滴泪成冰,愿将己身之寿,减一半与你母亲。因你至孝,感动天地。今吾神传上帝敕令,将冬天变做春天。今夜三更时分,命大众神祗降甘露瑞雪,满山遍峪,但有桑树,都生了椹子,任你摘来,与你母亲食用,自然病体安愈。你听者,这孝乃万善之本,百行之源。忠孝乃人之大节也,非忠不以为巨,非孝不以为子。凡人子事亲之际,无所不用其诚。要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此是人子之大孝也。你听者:父母恩深比昊天,嗟乎病体实堪怜。子行大孝诸神祐,永播芳名万古传。(正末拜众神科,云)感谢上圣也。(唱)
【后庭花】我怎消的众神灵下紫霄,驾祥云香雾绕。凛凛神威人,堂堂美像貌。赴天朝,亲传敕诏。为慈亲病重倒,因愚男尽孝道。后园中诚意祷,感天神来护保。枯桑上长出嫩条,香甘甘子结的饱。我摘将来盘内托,母亲行将孝意表,母亲行将孝意表。(增福神云)你那母亲,若食了这桑椹子,可自然病体安乐也。(正末唱)
【青哥儿】吃了呵但能得尊堂、尊堂安乐,我做一坛水陆、水陆大醮。(增福神做推正末科,云)休推睡里梦里。(众神随下)(正末醒科)(唱)呀!原来是一枕南柯梦已觉。恰才那空中神道,与小生梦里相交,细说根苗,着我欢展眉梢。小生这些时耽着忧怀着闷受煎熬,恰才呵听说罢喜孜孜开怀抱。
(旦儿上,云)蔡顺,你为何大惊小怪的?(正末云)大嫂,你不知。我因母亲思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寒冬天气,无处寻取。我恰才祷告上天,觉一阵昏沉,睡着了,梦见增福神同家宅六神来托梦。增福神言说,因我孝心感动天地,把冬天变做春天。今夜三更时分,着大众神祗降甘露瑞雪,满山遍峪,但是桑树,都结桑椹子。着我摘来,孝奉母亲,他自然无病也。(旦儿云)蔡顺,你的孝意真诚,因此上有这等感应也。(正末云)兀的不天色阴了也。(旦儿云)蔡顺,这天色定然是雪也。(正末云)兀的不欢喜杀小生也。(唱)
【尾声】可又早飕飕的风力峭,惨惨的冻云罩。他道是三更时分雪花飘,小生我深山中摘桑我可也不惮劳。怎敢把神灵违拗?(云)小生摘将那桑椹子来,母亲若吃下去呵。(唱)恰便是灵丹入腹可又早病儿消。(同旦儿下)
第三折
(桑树神上,云)园内开花我最奇,封为绫锦树神祗。蚕虫食叶生丝广,结果能充腹内饥。吾神乃桑树神是也。我枝叶荣旺,生长青肥。桑条弄翠影,桑叶有阴浓。那山妻采叶,喜柔条续续连青。稚子攀枝,爱紫椹重重带黑。吾神根蟠数丈,岁久年深,助蚕作茧,广织纱罗。吾神在园林中显耀,惟我独魁也。奉上帝敕令,封君神为绫锦之神。今因凡间有一人,姓蔡,名顺,字君仲。此人平生本分,孝顺双亲。因他母亲病体不安,如今冬寒天气,思想桑椹子食用。为此人孝心感动天地,奉上帝敕令,今夜三更时分,着大众神祗降甘露瑞雪,着吾神树上生桑椹子出来。蔡顺摘去,侍奉他母亲食用,就着他母亲病体安康。既有敕令,不敢有违。吾神往山林中知会众神,走一遭去。蒙敕令亲到山场,着那遍树上枝叶荣芳。桑椹子今宵就结,与蔡顺孝奉萱堂。(下)(风伯领鬼力上,云)巽位当权显耀雄,扬尘簸土罩乾坤。喜时清气人皆爽,怒后掀翻太华峰。吾神乃上界风伯神是也,专管一年四季和炎金朔。吾神随雷电震动乾坤,助飞雹浑弥宇宙。喜时尘土不动,怒时巨浪翻波。刮的那太岳山头岚峰动,地轴天关上下摇。今为下方为人者,姓蔡,名顺,字君仲。此人坚心孝道,因他母亲病体不安,思想桑椹子食用。况值冬寒时月,无处求取。此人至孝,感动天地,将冬天变做春天,着俺众神祗今夜三更时分,降甘露瑞雪,将山林下桑树,都滋长椹子出来,着蔡顺摘去,侍奉他母亲,病体自然痊可。吾神领了上帝敕令,待众神来时,自有主意。鬼力望者,这早晚众神敢待来也。(雪神同雨师领鬼力上)(雪神云)万里冰花六出寒,满空祥瑞蔽天关。顷刻变成银世界,须臾妆作玉江山。吾神乃上界雪神是也,这一位是雨师。吾神居于琉璃之宫,玉树之洞,住西天佛国世界。按乾坤之道,而分阴阳。温则为雨露,寒则成霜雪,能滋五谷,尽喜万民。今因下方有一人,姓蔡,名顺,字君仲。他母亲病体不安,孝心感动天地。上帝命俺众神,将冬天变做春天。今夜里三更时分,着吾神降雪,尊神降雨。将山中桑树,都生椹子,着蔡顺摘去,奉母病愈,方显俺的顺天感应也。有风神在空中等侯,速驾云端,走一遭去。远远的不是风神在此?(做见科)(雪神云)呀、呀、呀,吾神来迟,乞恕其罪也。(风神云)尊神,因蔡顺一事,既蒙上帝敕令,不敢有违。等雷公、电母来时,俺同降甘泽瑞雪,生出桑椹,救蔡顺的母亲病证。云头起处,敢是雷公、电母来也?(雷公、电母领鬼力上)(雷公云)隐隐声闻万里惊,电光雨势遍山村。天下一声雷震地,人间万物已知春。吾神乃上
界雷公是也,这一位是电母。吾神形容猛壮,性烈刚强,震塌乾坤,劈开山岳。惊枯木而发生,震蛰虫而出户。怒轰云汉,恶荡百川。今因下方有一人,姓蔡,名顺,字君仲。他母亲染病,想桑椹子食用。有蔡顺孝心,感动天神。上帝命俺大众神祗,今夜三更,降甘露瑞雪,满山林中,但是桑树,都生桑椹子,着蔡顺摘去奉母治病,方显神灵鉴察也。俺众神既奉敕令,不敢有违。今有风神在空中等侯,电母,俺去来。那云端里,兀的不是众位尊神在此?(做见众神科)(雷公云)众位尊神,吾神与电母来了也。(风神云)雪神、雨神、雷公、电母,都来了。您众位尊神,为因下方蔡顺奉母一事,您都知上帝敕令么?(众神云)俺都知上帝敕令也。(风神云)既知上帝敕令,俺神灵岂敢有违?天色已晚也。今夜至三更,吾神显耀威力,起一阵寒风,着雪神微微的降一阵瑞雪。等雪住时,吾神再助一阵和风,将冬天变做春天。着雷公发一声霹雳,震动山林,电母荧煌闪烁,光走金蛇,雨师下一阵甘雨。着遍山野桑树上,舒青叶,长翠条,都生出桑椹子来,着蔡顺摘奉母亲,病体指日而安,方显神灵感应也。鬼力,是多早晚时候也?(鬼力报科,云)报的尊神得知,夜至三更也。(风神云)夜至三更也。您众神祗各显神力,吾神刮起寒风来。兀的不寒风起了也。(众神云)是好寒风也。(风神云)雪神可随着这风,下一阵瑞雪。(雪神云)吾神降一阵瑞雪。兀的雪下了也。(众神云)是好大雪也。(风神云)雪够了也。吾神将冬天变做春天,助起这和风来。兀的不和风起了也。(雷公云)吾神显耀威力,震一声霹雳。兀的不雷响了也。(雷响科)(众神云)是好雷声也,(风神云)电母,可随着雨师,行一阵甘雨者。(电母云)吾神掣起这电光来。(雨师云)吾神行一阵雨。兀的不雨下了也。(众神云)是好甘雨也。(风神云)风雷雨雪都有了。吾神不敢久停久住,俺众神只回上帝话,走一遭去。一夜枯桑尽发荣,寒冰天气转东风。年高母疾重安乐,着他寿享人间百岁终。(同下)(延岑领偻儸上,云)几番摆阵靠山崖,阔剑长枪雁翅排。半垓劣缺搊搜汉,俺这里杀死敌军誓不埋。某乃五娄大王延岑是也。某幼习战策,广看兵书,英雄出众,胆略过人。有拔刀相助之威,扶弱欺强之志。因我在前,路见不平,致伤人命。自己出首到官,谢勘官可怜,将我迭配郑州牢城。行至半途,值着风雪,身上单寒,肚中饥馁,去蔡员外家乞讨茶饭来。不料蔡员外的夫人,他也姓延。因与我同姓,认义我为侄男,我拜他两口儿做父母。老夫人跟前,止生了一子,名唤蔡顺,此人十分孝顺。多蒙老员外
斋发了我暖衣一套,白银十两,又与了解子钱物。谁想那解子施恻隐之心,半途中开了枷锁,放了我。某不敢回家,不得已我也聚集了五千人马,在此山中落草为寇。这山名为五娄山。俺这里高山崄崚,阔涧湾环,山岭崚。,道路崎岖,树林密稠,水波汹涌。某声名传四野,敌兵唬胆寒。俺这里水欺东大海,山压太行山。人见某英勇,就呼某为五娄大王。某虽为贼盗,仗义疏财,索性公平,不夺小客之钱,岂图他人富贵。昨夜三更,下了一阵大雪,天气如春之暖。忽然雷声响亮,电掣金光,又下了一阵甘雨。未知主何凶吉?那山林中则怕有惊出来的狼虫虎豹,某如今领着半垓小偻儸,巡山走一遭去。昨宵雨雪净尘垓,今日英雄下峻崖。这一去军收锣鼓登山寨,马驮虎豹上山来。(同下)(正末同兴儿提篮儿上)(正末云)小生是蔡顺是也。昨日梦中见增福神,言说小生孝心感动神天,道三更时分,降甘泽瑞雪,那山林中,但是桑树上,都生出桑椹子来,任小生摘来,侍奉母亲。三更前后,果然降了一阵雪,下了一阵雨。小生今日,将着篮儿去山中摘桑椹子,走一遭去。俺母亲似这等身体不安,几时是好也?(唱)
【中吕】【粉蝶儿】每日家腹内思量,则我这孝心肠岂能敢忘?忧的是老尊堂卧枕眠床。我可便受驱驰,耽辛苦,满腹愁何曾展放?不由我心内忄西惶。俺母亲害的个病容颜,全不是旧时模样。
(云)则不小生行孝,想古者多有行孝之人也。(兴儿云)小哥,想上古贤人,那几个行孝?区区愚鲁,不知古往之事。小哥,试说一遍兴儿听者。(正末唱)
【醉春风】有一个董永卖亲身,黄香扇枕凉,郯子鹿乳奉萱堂。这三人万代可便讲,讲。则愿的老母安康,病体健,町便是俺子孙兴旺。
(兴儿云)小哥,昨夜三更,舒手不见掌。刮了阵风,下雪下雨,雷声闪电,一夜无休。雷骨碌碌的响将来,赶着我打,唬的我跪在灶窝里躲了。那雷骨碌碌响着寻我,他寻不着我也。他说:罢,罢,我还响了去罢。(外呈答云)诌弟子孩儿,得也么?(正末云)增福神说道:三更前后,降甘泽瑞雪,山中就有桑椹子,着我摘将来,侍奉母亲。果然降了一阵雪,下了一阵雨。这的是人有所愿,天必从之。(唱)
【迎仙客】昨夜个瑞雪飘,雨汪洋,仰天外黑黯黯可便云雾长。融融的便暖如春,轰轰的便雷震响,影影的便电走金光,感应的祥瑞舞甘泽降。(兴儿云)小哥,你看这山林中,青山绿水,有如画意,堪入丹青之手也。(正末云)不觉的来到这大山中,是一派好山色景致也。(唱)
【红绣鞋】看山色晴岚一样,看山峰高彻空苍,看山景叠翠蕊芬芳。看山林难描画,看山涧水流长,端的是山中堪玩赏。
(云)我贪看这山中景致,可忘了去寻桑树。我转过这隅头,下的这山坡来。兀的不是个桑园。(做惊科,云)呀、呀、呀,你看这园中桑树上,都结下椹子。感谢神天保佑。小生放下这篮儿,我摘这桑椹子者。(兴儿云)小哥,你便摘,我便口赛。撑杀我,往家抬。(外呈答云)得也么?(正末做摘桑椹子科)(唱)
【上小楼】我这里不索自忙,桑椹子园中开放。我可便举手攀枝,摘将下来,侍奉萱堂。一半红,一半黑,篮中各放,我这里便谢天公可怜垂降。(云)我将这椹子,摘满这篮儿也。(做提篮儿科,云)小生觉我这身子,有些困倦。我在这桑树下,暂且停止者。(兴儿云)小哥,我跟着你张罗这一日,我也打个盹,看有甚么人来?(延岑领偻儸冲上,云)巡山采猎独强霸,纵横放荡任非为。某乃是延岑也,领小偻儸去那山前山后,巡绰了一遭。不知怎生这山中,但是桑树,枝叶发生,都长出桑椹子来,好是奇怪也?小偻儸摆布的严整者。兀的不是个桑园?你看这桑树长的这等荣旺。(做见正末科,云)兀那桑树下,立着个年纪小的后生,领着个小厮,将着个篮子采桑。这厮好大胆也。小偻儸与我拿将他过来者。(偻儸云)理会的。(做拿正末科,云)过去跪者。(正末做跪科,云)太保饶性命。(兴儿云)太保留命喝汤罢。(延岑云)兀那厮,这是俺的境界,你怎敢在此采桑?侵犯我这山中。你这厮好大胆也。(偻儸云)大王,这小的倒将息的肥肥的,宰了罢。(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正末唱)
【幺篇】看了恶相貌,不由我心下慌。(延岑云)小偻儸,把这厮拿到山寨上,我慢慢的问他。(正末唱)他可便口口声声,忙传将令,拿去山岗。可惜了这桑椹子,孝敬礼,萱堂想望,屈沉了那增福神梦中显像。
(延岑云)来到这山寨上也。小楼儸,把那厮拿过来。(偻儸云)理会的。(正末做跪科)(延岑云)兀那厮,某在这五娄山落草为寇,一任那强兵猛将,谁敢来侵犯我这境界,你怎敢私来采桑?可不擒住了他的征夫,捉住的败将,某难以饶免。兀那厮,你是那里人?姓甚名谁?说的是,我自有个存活,若说的不是呵,小偻儸打下涧泉水,磨的刃锋利,某亲自下手也。(兴儿云)我说你有手,我也有手。你杀了他,管替他偿命。(外呈答云)得也么?泼说。(正末云)太保饶性命,听小生说一遍。小生乃汝南人也,姓蔡,名顺,嫡亲的四口儿家属:父亲蔡宁,母亲延氏,妻乃李氏。告太保可怜见。(延岑做沉吟科,云)母亲延氏?你莫不是蔡员外的儿男么?(正末云)小生是蔡员外的儿男。(延岑做惊科,云)险些儿不伤害了兄弟性命?天也,正是云影万重高士梦,月明千里故人来。(做扶正末科,云)兄弟,请起请起。你认的我么?(正末云)小生不认的太保。(延岑云)兄弟,你忘了我也。说兀的做甚?当日个感父母救我恩临,在山寨切切于心。今日个巡山采猎,见兄弟独立山林。听说罢家乡姓字,胜如得万两黄金。兄弟你是贵人多能忘事,则我是披枷锁迭配延岑。(正末云)原来是哥哥延岑。你怎生到这里来?(延岑云)兄弟,感谢母亲认义了我,与我了衣服盘缠,又与了我解子银物。多蒙那解子至半途中,施恻隐之心放了我。某难回故乡,就在那五娄山落草为寇,不想今日偶然间遇着兄弟。某一时间言语冲撞,恕某之罪。兄弟,一双父母安康么?(正末云)哥哥不知,今有母亲身体不安,想桑椹子食用。因小生孝心有感,神天保佑,冬月天气,生出桑椹子来。您兄弟摘他在盘中,回家侍奉老母。不想遇着哥哥在此也。(延岑云)原来母亲不安?兄弟有此孝敬,感动天地神灵,降生桑椹子。兄弟,你乃是贤哲君子也。小偻儸将那牛蹄粳米来者。(偻儸拿砌末,云)理会的。(延岑云)兄弟,无物可奉。山林野物,牛蹄一双,粳米三斗,你将去家中,侍奉父母亲。休嫌轻微也。(正末云)多谢哥哥厚礼也。(延岑云)兄弟,拜上母亲。我曾对天发誓:逢贤必住。等你回去了时,我将众兄弟小偻儸都散了,再不为贼盗也。如今大汉圣人,差官各府州县道,招安文武将士,量才擢用。某若到朝中,见了圣人,倘得任用了我呵,某定然保举你为官,报答父母之恩也。(正末云)谢了哥哥也。(唱)
【耍孩儿】愿哥哥腰金衣紫为卿相,稳做着皇家栋梁。三檐伞下气昂昂,保忠臣护国安邦。则愿的功高位至官一品,竭力芳名万载扬。非夸奖,博一个乌靴象简,五带罗裳。(延岑云)兄弟言者当也,我则今日星夜长行也。(兴儿做背砌末科,云)这个东西,定是我背着。我说老延,你就不与我个牛蹄儿吃?(延岑云)兄弟稳登前路,多多拜上父母也。(正末云)哥哥,您兄弟知道了也。(唱)
【尾声】哥哥你说的是壮士言,到京师见帝王。则要你去邪归正为良将,治国安邦万人讲。(同下)(延岑云)兄弟去了也。则今日将手下众兄弟都散了,某星夜起程,往京师见圣人,走一遭去。则今日便索登程,促行装亲赴神京。若为官举荐蔡顺,俺两个享富贵青史标名。(同下)
第四折
(卜儿同蔡员外领家童上)(卜儿云)药饵难医心上病,晨昏起坐要人扶。老身延氏,为因身体不安,朝则忘餐,夜则废寝,服药不效。我忽然思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冬寒时月,无处寻取。有孩蔡顺,尽孝道之心,今日早间,去那深山中寻桑椹子去了。老的也,可怎生这早晚,还不见孩儿来?(蔡员外云)婆婆,如今是寒冬天气,此物未知有无。婆婆,你少要忧心也。家童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家童云)理会的。(正末做盘中捧桑椹子,同兴儿背砌末上)(正末云)小生蔡顺。谢天地可怜,到于山中,摘了这满满的一篮桑椹子。又遇着哥哥延岑,他听知的母亲不安,奉牛蹄一双,粳米三斗,着我将来,侍奉萱亲。兴儿,休误了母亲食用。将着这桑椹子,献母亲去来。(兴儿云)小哥行动些。奶奶正想中间,若奶奶口赛下这桑椹子去,管情百病消除了也。(正末云)兴儿,你说的是。想俺这孝道的人,天公可也不曾亏负了俺也。(唱)
【正宫】【端正好】想怀耽,生身意,我可也报不的老母驱驰。则我这孝心肠感动天和地,俺可便行孝道无邪伪。
【滚绣球】我焚香祭赛天,不觉的睡似痴,见一位增福神降临凡世。他说道半夜间响一阵春雷,他道是纷纷雪乱飞,淙淙雨下的疾。两般儿委实奇异,我醒来时心内猜疑。到天明我走到山间下,谁承望园内开花结果肥,椹子皆垂。
(云)俺可早来到也。家童报复去,道俺来了也。(家童云)理会的。报的奶奶得知,有小哥来了也。(卜儿云)着孩儿过来。(家童云)理会的。过去。(正末见科,云)母亲,孩儿来了也。(卜儿云)孩儿,你来了也。你寻的桑椹子,可是有也无?(正末云)母亲,有了也。这盘中托的是桑椹子。(卜儿惊科,云)孩儿也,如今是寒冬时月,万木凋零,你可那里得这桑椹子来?(正末云)母亲,桑椹子非同容易。母亲,尽您孩儿孝道之心,你用几个者。(卜儿云)孩儿也,我正想他食用。将来我吃几个者。(正末做捧桑椹子科,云)母亲,请食用几个。(卜儿做吃科,云)孩儿,这桑椹子好甜也,我吃下去如酥蜜一般,甚是甘美,滋味更佳也。(兴儿云)我把你这个馋嘴的老婆子。(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骂的巧。(正末唱)
【倘秀才】这桑椹子犹如蜜水,(卜儿云)孩儿也,我吃了他呵,正是如渴思浆,如热思凉也。(正末云)母亲,这桑椹子,休看的他轻也。(唱)他可便蒙雨露开花蕊。(卜儿云)将来,我吃几个。(兴儿云)你倒会吃也。(正末唱)母亲心内思想腹内饥。(卜儿云)孩儿也,我这病看看的好将来了也。(正末唱)好着我生欢悦,展愁眉,请街坊庆喜。
(卜儿云)孩儿也,我吃的够了,与我抬了者。(正末云)母亲,这一会儿病体如何?(卜儿云)孩儿,我吃了这桑椹子,这一会身体,如旧时一般,觉我无了病也。(正末唱)
【叨叨令】母亲,也你似那旧时节脉息通胸胃;恰才无半霎,就把你灾除退;(卜儿云)孩儿也,多亏你行这等孝顺之心也。(正末唱)则我这孝心肠,感动天和地。则愿的母亲年高百岁身荣贵。兀的不喜欢杀也波哥,喜欢杀也波哥,俺一家儿办诚心酬谢天和地。(卜儿云)孩儿,我不问你别。这牛蹄、粳米,是那里来的?(正末云)母亲,您孩儿大山之中,遇着延岑哥哥来。(卜儿云)延岑?他不去郑州迭配牢城,他在山中做些甚么那?(正末唱)
【脱布衫】他在那大山里落草为贼,领半垓人马围随。枪刀摆旗幡招展,狼虎般显耀威势。(卜儿云)他在山中落草为寇,你可怎生撞见他来?(正末唱)
【小梁州】他把我拿到营中要整理,谁承望认的真实。从前已往说端的,他喜则喜今日会,他说道相见在山溪。
(卜儿云)孩儿,你在山中见了延岑,威严摆布,你惊慌之中,说些甚么来?(正末唱)
【幺篇】我说道母亲病体实难退,俺哥哥听说罢两泪双垂。他说道老母的恩,心中记,他将这牛蹄和粳米,奉老母病将息。
(卜儿云)此人他倒不忘俺旧日之恩也。(正末云)母亲,延岑哥哥说道:逢贤必住,永不为盗。散了手下偻儸,他去京师见大汉圣人去了。他若为官时,要举荐您孩儿为官哩。(卜儿云)孩儿也,可难为此人的心。俺慢慢的说话,看有甚么人来?(外扮使命上,云)雷霆驱号令,传宣急急行。自离京师地,不觉至门庭。小官天朝使命是也,为因延岑文武兼济,刀马过人。圣人见喜,官封太尉之职。延岑就举保一人,乃是蔡顺,说此人忠孝双全。奉圣人的命,着小官将着玄纁丹诏,来取蔡顺全家,前赴京师,加官赐赏。我问人来,这一家儿便是。不索报复,我自过去。(做见科,云)您一家儿都在此也。小官不是别人,乃天朝使命是也。(正末云)呀、呀,天朝使命大人到此,小生有失迎接也。(使命云)谁是蔡顺?(正末云)小生便是。(使命云)你是蔡顺?如今朝中有一人,乃是延岑,在圣人跟前,举保你为官,着小官取您一家儿全赴京师,加宫赐赏。(正末云)家童装香来。(家童云)理会的。(正末做焚香拜科,云)感谢圣恩。家童快安排果卓,管待使命大人。(使命云)小官不敢饮酒。贤士收拾行装,便索登程。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圣人的话,走一遭去。则今日就盼途程,乘骏马款款先行。到京师亲临丹陛,一一的奏说叮咛。(下)(正末云)使命大人去了也。父亲、母亲,俺则今日收拾行装,赴京师走一遭去也。(唱)
【尾声】传宣降诏非容易,整办行装不可迟。俺可便盼程途去得疾,到朝中文武齐。见圣人习礼仪,受官爵加重职,俺博一个衣紫腰金贺声喜。(同众下)
第五折
(殿头官领张千上,云)朝去稳登金勒马,来时袍袖惹天香。小宫殿头官是也。为因大将延岑,到于京师。因此人文武兼济,刀马过人,圣人见喜,官封太尉之职。有延岑就举保他的认义兄弟,乃是蔡顺,说此人忠孝两全。圣人差使命,取蔡顺一家儿,全赴京师。今日早朝,奉圣人的命,着小宫在这相府中,聚众大人安排酒肴,与蔡顺并他一双父母庆喜,就与他加官赐赏。令人觑者,若众大人来时,报复我知道。(张千云)理会的。(延岑云)举善荐贤施政化,报恩答义显忠良。某延岑是也。想某在五娄山落草为寇,因见兄弟蔡顺贤明至孝,我就将手下半垓偻儸都散了,来到京师。见了圣人。为某文武兼济,官封重职。我就举保蔡顺忠孝兼全,圣人就着使命,将蔡顺并他父母,都取至京师。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酒肴,与蔡顺全家庆贺,就要加官赐赏。某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某来了也。(张千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延将军来了也。(殿头官云)道有请。(张千云)理会的。有请。(见科)(延岑云)大人,某来了也。(殿头官云)将军少待,等蔡顺一家儿来全,俺庆饮酒。这早晚敢待来也。(刘晋能同周景和上)(晋能云)为囚孝于身荣贵,远远登途贺喜来。老夫刘普能是也,这一位长者,是周景和。为因蔡顺于家行孝,于国尽忠。有延岑不忘他父母之恩,举保他一家儿,都取到京师。俺不避路途艰难,来到京师。说今日相府中安排筵宴,与蔡顺一者庆贺,二者加官。周景和,俺须索走一遭去。(周景和云)员外,看了蔡顺能文出众,才智过人,理当为官享禄,皇天岂负贤人也。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有刘普能、周景和来见大人。(张千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刘普能、周景和来见大人。(殿头官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的。过去。(见科)(刘普能云)大人,俺村野之人,乍入京华,辇毂之下,幸遇大人尊颜,实乃老拙万幸也。(殿头官云)您两个员外,且一壁有者。(夏德闰、仇彦达同上,夏德闰云)不因侍亲行孝道,怎得加职表门闾。老夫夏德闰是也,这一位长者是仇彦达。今因蔡顺至孝感天,冬月降生桑椹子。又蒙延将军举保,说此人忠孝双全,将他一家儿都取至京师,赐宅居住。俺都至京师,与蔡顺特来庆贺。(仇彦达云)夏员外,似蔡顺忠于君王,孝于父母,人间少有,堪受皇家官位。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夏德闰、仇彦达,来见大人。(张千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夏德闰、仇彦达,来见大人。(殿头官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的。过去。(做见科)(夏德闰云)大人,乡村老叟,无德无能
,今日得观大人尊颜,是老拙之万幸也。(殿头官云)您两个员外,且一壁有者。(净王伴哥同白厮赖上,王伴哥云)俺二人登山涉水,与君仲特来庆美,又无甚羊酒花红,真一对虚头油嘴。自家王伴哥便是,这个是兄弟白厮赖,与俺两个,是出名的旧油嘴。今有蔡顺,取至京师,俺两个也来与他作贺。俺是精光棍,又无个驴儿骑,一路上则是步行。我若走的困了,着兄弟背着我走;兄弟走的困了,我大棍子赶着他跑。(外呈答云)你可怎生不背他?(王伴哥云)我管他死么?(外呈答云)得也么?这厮没天理。(王伴哥云)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筵宴,与蔡顺一家儿庆贺,又说加官赐赏。兄弟,俺偌远的走这一遭,是要口赛要吃。(白厮赖云)今日我吃的醉了。哥,你若不背着我走,我把耳朵都咬掉了你的。(外呈答云)得也么?(白厮赖云)可早来到相府门首也。兀那小张儿,报复去,道有白厮赖、王伴哥来了也。(张千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白厮赖、王伴哥来见大人。(殿头官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的。过去。(二净做见科)(王伴哥云)老大儿,小人来了也,有甚么东西,拿来先吃着耍儿。(殿头官云)且一壁有者。(蔡员外同卜儿、旦儿上,蔡员外云)幸能子孝为良器,祖宗光显感洪恩。老夫蔡宁是也,这个是我夫人延氏,这个是媳妇润莲。为因延岑举荐蔡顺为官,谢天恩可怜,将俺全家儿都取到京师。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筵宴,与俺庆贺,就加官赐赏。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蔡顺家属来了也。(张千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蔡顺家属来了也。(殿头宫云)道有请。(张千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蔡员外云)老汉三口儿家属,来见大人。(殿头宫云)蔡员外,您且一壁有者。令人门首觑者,若蔡顺来时,报复我知道。(张千云)理会的。(正末上,云)小生蔡顺是也。有延岑哥哥,到于朝中,因此人文武兼济,弓马熟闲,圣人见喜,重赏加官,哥哥就举荐小生。谢圣恩可怜,将我一家儿,都取到京师。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筵宴,与小生全家儿庆贺,加官赐赏,须索走一遭去。谁想有今日也?(唱)
【双调】【新水令】圣明天子重英贤,选儒流武十两件。文官扶社稷,良将保山川。端的是万载流传,今日个排筵会没佳宴。
(云)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蔡顺来了也。(张千云)理会的。报的大人得知:有蔡顺来了也。(殿头官云)道有请。(张千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正末云)大人,小生蔡顺来了也。(殿头官云)久闻贤士有颜回亚圣之学,曾参养亲之孝,仁宏德厚,至善光辉。忠尽于君,孝尽于亲。忠孝两美,驰名于朝野之中。未尝得睹尊颜,今日一见,乃小官万幸也。(正末云)不敢,不敢。量小生一介寒儒,素无才德,何敢着大人挂念也?(唱)
【驻马听】幼小轻年,腹内孤穷学问浅。(殿头官云)久闻贤士广览诗书,堪为辅弼之臣也。(正末唱)你不劳挂念,我是个白衣人怎到得玉阶前?(殿头官云)说贤士文胜颜回,孝越曾参也。(正末云)大人,小人怎敢比先贤古人也?(唱)鸾鸣胜似鹊声喧,凤飞比雁先腾远。我自言小生腹空虚,怎敢比高儒选?(殿头官云)蔡秀才,你与延岑厮见者。(二人做见科)(正末云)呀、呀,哥哥,受您兄弟两拜。(做拜科,云)您兄弟多亏哥哥,在圣人跟前举荐。若不是哥哥,小生焉能得到此也?(延岑云)不敢。虽是某举荐,况贤弟忠孝双全,名播于朝。据贤弟胸怀锦绣,口吐珠玑,乃翰林之魁首,堪可国家任用。今日峥嵘,方称贤弟之志也。(正末云)多谢了哥哥抬举也。(殿头官云)蔡秀才,当日你母亲不安,冬寒天气,思想桑椹子食用,你可怎生得桑椹子来?你说一遍,我试听者。(正末唱)
【雁儿落】想当日萱亲疾病缠,他可便思绫锦当时见。小生我焚香祷上苍,一梦里神灵现。(殿头官云)你梦中见神灵,说甚么来?(正末唱)
【得胜令】呀!他道是冬寒月变做春天,半夜里雪花舞雨涟涟。枯桑上生棋子,我醒来时把梦圆。走到那山前,桑椹子都生遍。摘将来新鲜,俺母亲吃了体自然。
(殿头官云)谁想你至孝,通天地,感神灵,将冬天变做春天,枯桑荣旺,椹子发生,保养你母亲病体安愈。孝名扬于四海,贯满皇都,堪可排宴庆贺。令人抬上果卓来者。(张千云)理会的。(做抬果卓科)(殿头官云)将酒来,这杯酒先从蔡员外来。老员外满饮此杯。(蔡员外云)老夫不敢。大人先饮。(殿头官云)今日与你一家儿庆贺,理当你先饮,不必过谦也。(蔡员外饮科,云)老夫依命先饮。(殿头官云)将酒来。这杯酒老夫人饮。(卜儿云)大人请。(殿头官云)这个孝道的儿男,不枉了生于人世。你满饮此杯。(卜儿饮科,云)老身饮。(殿头官云)再将酒来。这一杯酒贤士饮。(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着大人如此用心?大人先请。(殿头官云)贤士饮过者。(正末饮科,云)不敢。小生饮。(殿头官云)贤士,小官奉命大开筵宴,一者与你庆贺,二者加官赐赏。此一会非同小可也。(正末唱)
【沽美酒】感大恩重呵怜,招杰士纳英贤。端的足德似尧汤千古传,万万载江山固坚,好收成谢冲天。
【太平令】四海内年年纳献,掌山河一统安然。万回来偏邦朝见,文共武随龙迁转。呀,谢圣恩可怜,就传将俺来便宣,一一的拜舞金銮宝殿。
(殿头官云)您众人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大汉朝一统疆封,万万载海晏河清。普天下军民乐业,遍乾坤黎庶安宁。则为这蔡君仲奉亲至孝,播皇朝万古留名。因老母身生疾病,告苍天血流成冰。办虔心至诚发愿,梦寐中亲见神灵。三更鼓甘泽雪降,绫锦树椹果枝生。他去那山林中摘来奉母,救萱堂一命安存。感延岑临朝举荐,一家儿取至京城。蔡顺封翰林学士,李氏赠贤德夫人。蔡员外治家有法,年高迈冠带荣身。老夫人心慈性善,钦赏你个锭花银。众员外都赐表里,封官罢各自回程。圣人喜的是义夫节妇,爱的是孝子贤孙。今日个加冠赐赏,朝帝阙拜谢皇恩。
题目报恩义延岑举荐
正名降桑椹蔡顺奉母
花艳冶,柳欹斜,粉墙低画楼人困也。庭院星列,罗绮云叠,簇簇闹蜂蝶。
紫霞杯我辈豪侠,绿云鬟仕女奇绝。乌丝栏看醉草,红牙板唱声揭。别,同载七
香车。 避暑偶成
共翠娥,酌金波,湖上晚风摇芰荷。丝管情多,帘幕凉过,暑气尽消磨。扇
停风几缕柔歌,袜凌波一掬香罗。醉魂偏浩荡,诗兴费吟哦。睃,老子正婆娑。 秋闺
笼太纤,拜银蟾,恰团圆几时云又掩。尘淡妆奁,风透朱帘,无语望雕檐。
博山炉香冷慵添。阳春曲唱和难タ。新凉开扇影,清恨蹙眉尖。嫌,何处可消淹?
李辅之在齐州,予客济源,辅之有和。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
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孤负欢游。一尊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州!
 唐顺之
唐顺之 辛弃疾
辛弃疾 白居易
白居易 张寿卿
张寿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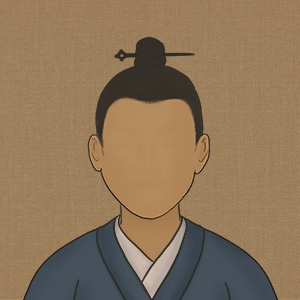 周文质
周文质 吴西逸
吴西逸 元好问
元好问 丘处机
丘处机 赵以夫
赵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