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痕新月渐渐挂上柳梢,仿佛眉痕。淡净的月彩从花树间透过,蒙胧的光华将初降的暮色划破。新月明艳便使人生出团圆的意愿,闺中佳人更深深拜月祈盼,祝愿能与心上人相逢在那花香迷人的小径。一弯新月就像两道美人的秀眉没有画完,一定是嫦娥还带着离恨别情。最令人喜爱的是,寥廓明净的天空上,那弯新月恰似宝帘上的帘铮,小巧玲珑。
月有圆亏缺盈,千古以来就是如此,不必细问究竟。我叹息吴刚徙然磨快玉斧,也难以将此轮残月补全。长安故都的太液池依然存在,只是一片萧条冷清,又有谁人能重新描写昔日清丽的湖山?故乡的深夜漫长悠永,我期待月亮快些圆满澄明,端端正正地照耀我的门庭。可惜月影中的山河无限,我却徒自老去。只能在月影中看到故国山河的象征。
注释
眉妩:词牌名。一名《百宜娇》。宋姜夔创调,曾填一首《戏张仲远》一首,词咏艳情。双调一百零三字,仄韵格。
新痕:指初露的新月。
淡彩:微光。淡一作“澹”。
依约:仿佛;隐约。
初暝:夜幕刚刚降临。
团圆意:唐牛希济《生查子》:“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圆意。”此处反用其意。
深深拜:古代妇女有拜新月之风俗,以祈求团圆。
香径:花间小路,或指落花满地的小径。
未稳:未完,未妥。
素娥:嫦娥的别称。亦用作月的代称。
银钩:泛指新月。
盈亏:满损,圆缺。
慢磨玉斧:玉斧,指玉斧修月。
金镜:比喻月亮。
太液池:汉唐均有太液池在宫禁中。
故山夜永:故山,旧山,喻家乡。夜永,夜长;夜深。多用于诗中。
端正:谓圆月。
云外山河:暗指辽阔的故国山河。
桂花旧影:月影。桂花影,传说月中有桂树,这里指大地上的月光。
参考资料:
赏析
江山已易主。在词人王沂孙那里。故国之意仍是一丝扭不断的情结。连新月也被词人赋予了这层含义。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永恒规律面前,词人希冀把握住一种必然。面对宗祖沉沦,今昔巨变之痛,词人借咏新月寄寓了对亡国的哀思。全词将赏月、观月,因月感怀作为线索,绵绵君国之思,全借咏月写出,托物寄怀,耐人寻味。
上片描绘新月,刻意渲染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极写它的妩媚动人。“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冥。”由“渐”字领起,刻画初升的新月,烘托出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新月如佳人一抹淡淡的眉痕,悬挂柳梢之上。新月渐升,月色轻笼花丛,轻柔的月色象无力笼花,若有若无地穿流于花间,不断升腾仿佛分破了初罩大地的暮霭。三句充满新意地写出新月的独特韵致。对清新美妙的新月,生出团聚的祈望。接着,“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深深拜”三字,写出“团圆意”的殷切期望。但同赏者未归,词人不免顿生“相逢谁在香径”的怅惘,欣喜和祈望一瞬间蒙上了淡淡的哀愁,新月也染上凄清的色彩。由憧憬变为怅惘,不觉以离人之眼观月。纤纤新月好象尚未画好的美人蛾眉,想是月中嫦娥伤别离之故,借嫦娥之态托出“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自伤孤独之情。
“画眉未稳”应和“新痕”。与紧扣“素娥”、“离恨”由月及人,虚托出词人委婉曲折的情愫。“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由月中嫦娥的象外兴感折回新月。在无垠的夜空中,新月象银钩似的遥挂在夜空。夜空浩茫,新月何其小也。秋空之“冷”,新月之“小”它使词人对新月的怜爱之情,具有一种幽渺的意蕴。
上片词人表达了对新月在浩茫宇宙中之渺小的怅惘之情,随之下片将笔一纵,大墨一挥“千古”振起,语意苍凉激楚。“千古盈亏休问”一语括尽月亮与人世来盈亏往复的变化规律。由此领悟到支配无限时间永恒规律的宇宙感,反观人世充满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容人问的悲哀。“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用玉斧修月之事,表现出极为沉痛的回天无力复国无望的绝望和哀叹。“休问”、“慢磨玉斧”(慢同谩,徒劳之意)、“难补金镜”的决绝之语,表达一种极其绝痛、惶惑和悲哀的情感。涵括着一种融历史透视和宇宙透视为一体的时间忧患意识。
“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总括历朝宋帝于池边赏月的盛事清景。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宋太祖曾临池饮酒,学士卢多逊作诗:“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周密《武林旧事》曾记载宋高宗和宋孝宗也有临池之举。王沂孙此词中的“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由感而发,寥寥几笔,写尽古今盛衰,此时已物是人非,情景凄凉之极。
“故山夜永”,“夜永”托出残月黯淡之景,象征亡国之哀。漫漫长夜中,永久无尽地煎熬着亡国遗民的心灵。至此,已将词人的亡国哀伤写到极致。“试待他、窥户端正”,奇峰另起,见出沉郁顿挫之姿。
“窥户端正”应上“团圆意”。故乡山河残破,设想他日月圆之时,“还老尽,桂花影。”桂花影,传说月中有桂树,这里指大地上的月光。月亮自是盈亏有恒,而大地山河不能恢复旧时清影,其执着缠绵地痛悼故国之情,千载之下,仍使人低徊不已。
唐人有拜新月之俗,宋人也喜欢新月下置宴饮酒。临宴题咏新月,也是南宋文士的风雅习尚。赏月观月、因月感怀,是贯穿全篇的线索。循着作者因新月而生的今昔纵横的意识情感流动轨迹,和新月相系的人情典事,寄托词人的怀国之情。
参考资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鹦鹉洲,凤凰楼,十年故人怀旧游。杜陵花,陶令酒,酒病花愁,不觉的今春瘦。
湖上送别
钓锦鳞,棹红云,西湖画船三月春。正思家,还送人,绿满前村,烟雨江南恨。
春日湖上二首
雨亦奇,锦成围,笙歌满城莺燕飞。紫霞杯,金缕衣,倒著接篱,湖上山翁醉。
舞绛纱,扣红牙,耳边玉人催上马。雪儿歌,苏小家,月淡梨花,醉倚秋千架。
春晚
看牡丹,倚阑干,宿酒乍醒攲髻鬟。燕初忙,莺正懒,帘卷轻寒,玉手调筝雁。
秋夜
雨乍晴,月笼明,秋香院落砧杵鸣。二三更,千万声,捣碎离情,不管愁人听。
黄桂
近玉阶,映瑶台,婆婆小丛岩畔栽。雁初飞,花正开,金粟如来,望月佳人拜。
一阵风,一阵雨,满城中落花飞絮。纱窗外蓦然闻杜宇,一声声唤回春去。
云笼月,风弄铁,两般儿助人凄切。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一声欲灭。
磨龙墨,染兔毫,倩花笺欲传音耗。真写到半张却带草,叙寒温不知个颠倒。
从别后,音信绝,薄情种害煞人也。逢一个见一个因话不说,不信你耳轮儿不热。
从别后,音信杳,梦儿里也曾来到。问人知行到一万遭,不信你眼皮儿不跳。
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
人初静,月正明,纱窗外玉梅斜映。梅花笑人休弄影,月沉时一般孤另。
八千里,愁万缕,望不断野烟汀树。一会价上心来没是处,恨不得待跨鸾归去。
研香汁,展素纸,蘸霜毫略传心事。和泪谨封断肠词,小书生再三传示。
实心儿待,休做谎话儿猜,不信道为伊曾害,害时节有谁曾见来,瞒不过主腰胸带。
江梅态,桃杏腮,娇滴滴海棠颜色。金莲肯分迭半折,瘦厌厌柳腰一捻。
思今日,想去年,依旧绿杨庭院。桃花嫣然三月天,只不见去年人面。
蝶慵戏,莺倦啼,方是困人天气。莫怪落花吹不起,珠帘外晚风无力。
他心罢,咱便舍,空担着这场风月。一锅滚水冷定也,再撺红几时得热。
相思病,怎地医?只除是有情人调理。相偎相抱诊脉息,不服药自然圆备。
心窝儿兴,奶陇儿情,低低的啀声相应。舌尖抵着牙缝冷,半合儿使的成病。
香罗带,玉镜台,对妆奁懒施眉黛。落红满阶愁似海,问东君"故人安在"?
青纱帐,白象床,晚凉生月轮初上。谁家玉箫吹凤凰,教断肠人越添惆怅。
如年夜,人乍别,角声寒玉梅惊谢。梦回酒醒灯尽也,对着冷清清半窗残月。
蔷薇露,荷叶雨,菊花霜冷香庭户。梅梢月斜人影孤,恨薄情四时辜负。
琴愁操,香倦烧,盼春来不知春到。日长也小窗前睡着,卖花声把人惊觉。
因他害,染病疾,相识每劝咱是好意。相识若知咱就里,和相识也一般憔悴。
黄叶青苔归路,屧粉衣香何处。消息竟沉沉,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因风吹去。(版本一)
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竟沉沉,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因风吹去。(版本二)
 王沂孙
王沂孙 司马迁
司马迁 张可久
张可久 张养浩
张养浩 乔吉
乔吉 马致远
马致远 阎选
阎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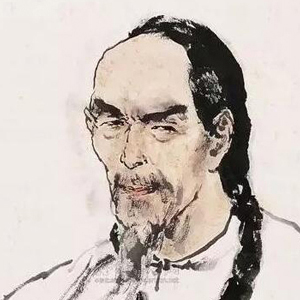 龚自珍
龚自珍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辛弃疾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