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歌
天朗气清日亭午,閒吟散食步廊庑。耳根彷佛隐雷鸣,又似波涛风激怒。
涛声乍过心犹疑,忽诧栋梁能动移。顷刻金甑相倾碎,霎时身体若笼筛。
厩马嘶蹶犬狂吠,智者猝然亦愚昧。悲风惨惨日无光,霎尔晴空成昼晦。
扶老携幼出门走,忙忙真似丧家狗。更有楼居最动摇,欲下不得心急焦。
心急势危肝胆碎,失足一堕魂难招。蚁走热锅方寸乱,两脚圈豚绳索绊。
窘逼转愁门户狭,攀援不觉窗棂断。如逢虎狼如触蠍,形神惝恍魂飞越。
偷眼视之但溟茫,满耳声闻唯窸窣。千家万家齐屏息,大儿小儿多避匿。
少选声停地始平,相顾人人成土色。地平踏稳相欣告,众口一时同喧噪。
老者无策少者疑,从此夜眠心不怡。东南虽缺地无缝,岂有妖物簧鼓之。
自是乾坤气吞吐,世人那得知其故。幸哉淡水尚安全,可怜嘉、彰成墟墓。
试问既震何重轻,消息茫茫归劫数。长歌赋罢心转愁,惊魂未定笔亦柔。
此情回首不堪忆,此身犹自随沉浮。安得长房缩地法,居吾乐土免烦忧。
林占梅,历史人物,是中国清朝官员。根据《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他于1802年上任台湾府儒学训导,隶属于台湾道台湾府,为台湾清治时期的地方官员,该官职主要从事台湾府境内之教育行政部分,受台湾府儒学教授制约,该官职亦通常为闽籍,语言可与台湾人互作沟通,事实上,教学上也以闽语为主,官话为辅。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
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
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
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
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
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閤,义旗已入长安宫。
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
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余年来观瀑屡矣,至峡江寺而意难决舍,则飞泉一亭为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悦,其体不适,势不能久留。天台之瀑,离寺百步,雁宕瀑旁无寺。他若匡庐,若罗浮,若青田之石门,瀑未尝不奇,而游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从容以观,如倾盖交,虽欢易别。
惟粤东峡山,高不过里许,而磴级纡曲,古松张覆,骄阳不炙。过石桥,有三奇树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结为一。凡树皆根合而枝分,此独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纵横丈馀,八窗明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笔研,可瀹茗置饮,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与之对枰。于是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顷之,又有曳杖声从云中来者,则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天籁人籁,合同而化。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带玉堂。正对南山,云树蓊郁,中隔长江,风帆往来,妙无一人肯泊岸来此寺者。僧告余曰:“峡江寺俗名飞来寺。”余笑曰:“寺何能飞?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僧曰:“无征不信。公爱之,何不记之!”余曰:“诺。”已遂述数行,一以自存,一以与僧。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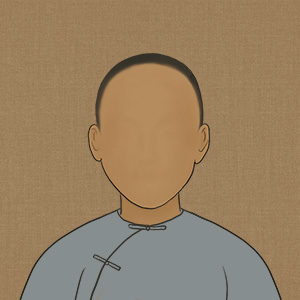 林占梅
林占梅 白居易
白居易 司马迁
司马迁 纪昀
纪昀 袁枚
袁枚 张可久
张可久 冯延巳
冯延巳 俞国宝
俞国宝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苏轼
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