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商人天还未亮就已起床,仍觉得此时出发已经太迟了。
高山之中有条捷径,在天色还很昏暗的时候赶路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和觊觎。
但不幸的是有盗寇埋伏在这条路上,当商人经过时,他们一拥而上。
金银财宝被人洗劫一空,空落落的钱袋子被丢弃在小路旁。
商人辛苦多年,在扬州购买了大宅,却没想到路遇劫匪,葬身荒野。
他的妻子此时不知不幸已经发生,正对着镜子细细整理自己的妆容,等待商人的归来。
注释
贾(gǔ)客:商人。古时特指囤积营利的坐商,古时候称行商为“商”,坐商为“贾”。后泛指商人。
发:出发。
疾路:捷径。
暗行:在天色还很昏暗的时候赶路。
寇盗:指抢劫的强盗。
委:丢弃,抛弃。岐:一作“歧”,路的分支。
扬州:今扬州,唐朝当时最著名、最繁华的都市,也是当时富商大贾的集散地。
此日:此时此刻。▲
创作背景
唐代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在全国各地,蕃镇节度使掌有地方政权与大部分兵权,不受唐王朝的统治。诗人为体现唐朝商人及其亲人的悲惨生活,写下了这首诗。
赏析
此诗内容不加雕饰,语言流畅,如行云流水一般,真实自然地表现了唐朝贾客(商人)及其亲人的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表达了诗人对唐朝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和伤感。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中,通过“起”、“言”、“行”等动作,写商人为了谋利,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暗行”照应“灯下起”,口口声声“发已迟”到“终不疑”,都可看出诗人炼句是颇费斟酌的。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两句承接上面,写贾客“暗行”引出的后果。“猛兽来相追”:既写出寇盗的凶残,又自然地引出商人可悲的下场。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这里不写贾客性命如何,却只说了钱财被抢光。其实写钱就是侧写人,而且是更深刻地刻画了人。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古人认为客死异乡是很可悲的,一般只有穷困潦倒的人才会遭此不幸。“扬州”是当时极为繁华的城市,死者家住扬州,有朱门大宅,竟落到如此下场,实在难以想象。仅此两句,已使诗的意境更为深邃了。
不料诗人笔锋一转,出语惊人:“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这一方尸骨已抛弃在荒山僻野,那一方尚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等待贾客归来。“当此日”三个字把两种相反的现象连接到一起形成对照,就更显得贾客的下场可悲可叹,少妇的命运可悲可怜。
诗人这种抒发感想的方法很值得借鉴,比直来直去地发一番议论强得多。这四句诗仿佛在讲客观事实,并不带丝毫主观的色彩。诗人通过几个很妥贴的意象来表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这种技巧,在唐诗中是常见的。▲
刘驾,唐(约公元八六七年前后在世)字司南,江东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中前后在世。与曹邺友善,俱工古风。邺先及第,不忍先归,待于长安。辛文房称其“诗多比兴含蓄,体无定规,兴尽即止,为时所宗。”(《唐才子传》卷七)其诗较有社会内容,如《反贾客乐》反映农民疾苦,《有感》抨击边将腐化,《弃妇》表现对被遗弃妇女的同情,都是晚唐较好的作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诗集一卷,《全唐诗》录存其诗六十八首,编为一卷。事迹见其《唐乐府十首序)) 、《唐摭言》卷四、《唐才子传》卷七。《全唐诗》录存其诗六十八首,编为一卷。
危径几万转,数里将三休。
回环见徒侣,隐映隔林丘。
飒飒松上雨,潺潺石中流。
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
望见南山阳,白露霭悠悠。
青皋丽已净,绿树郁如浮。
曾是厌蒙密,旷然销人忧。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栏杆 一作:阑干)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刘驾
刘驾 王维
王维 李曾伯
李曾伯 秦观
秦观 晏殊
晏殊 张泌
张泌 刘克庄
刘克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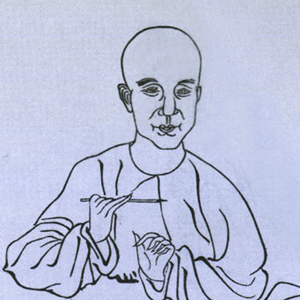 项鸿祚
项鸿祚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辛弃疾
辛弃疾